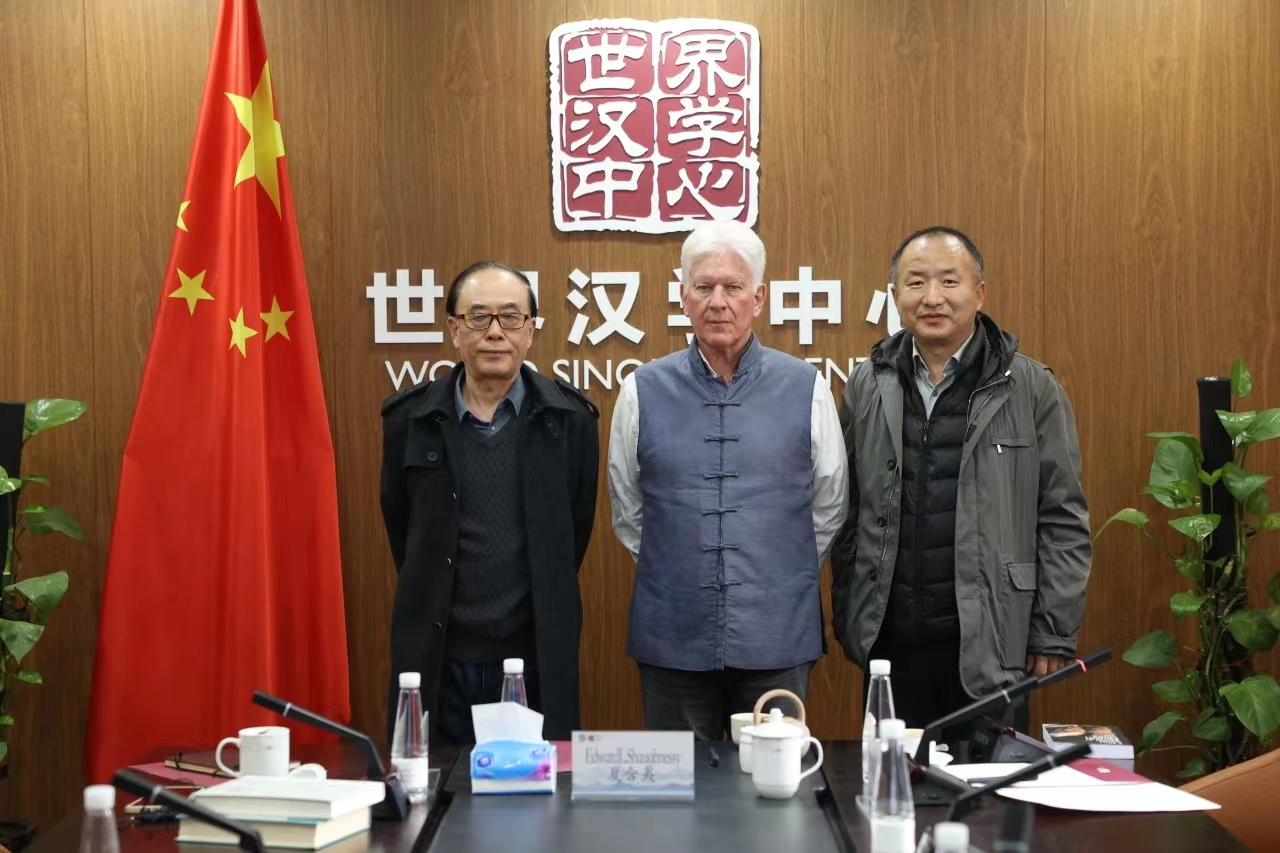金文京/段江丽:中国文学与东亚文学-文化圈
中国古代文学与东亚文学-文化圈
——金文京先生访谈录
段江丽
金文京先生,韩国籍,1952年3月出生于日本东京,1974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本科毕业;1976年京都大学大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毕业;1979年京都大学大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博士课程修了。现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韩国成均馆大学兼职教授、日本中国学会评议员、日本东方学会评议员、日本道教学会理事、(日本)中国社会文化学会理事等。曾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2005-2009),日本中国学会副理事长(2001-2005),台湾大学中文系客座副教授(1999-2000)。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在中日韩三国出版著作(含合著)20多部,发表论文及研究报告140余篇。主要代表作有(含合著):《三国演义的世界》、《〈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研究》、《中国小说选》、《花关索传研究》、《邯郸梦记校注》、《〈至正条格〉校注本》、《元杂剧研究——〈三夺槊〉〈气英布〉〈西蜀梦〉〈单刀会〉》、《元杂剧研究——〈贬夜郎〉〈介之推〉》、《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第1辑)》、《汉文与东亚训读文化圈》、《能与京剧》等等。本刊特委托北京语言大学段江丽教授就有关学术问题采访金文京先生,整理出此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段江丽 金教授,您好!我作为JSPS项目研究者,在您的直接帮助之下,来到京都大学人文所从事研究工作,并受《文艺研究》编辑部委托,就有关学术问题向您请教,深感荣幸!同时,对您的帮助,以及慨允接受访谈,深表感谢!
金文京 不客气。还要感谢你和《文艺研究》编辑部才是。
段江丽 刚刚听到的好消息,“角川财团学艺奖”近日揭晓,今年荣膺大奖的是您的大作《汉文与东亚训读文化圈》,在此谨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并请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奖项的性质。
金文京 谢谢!“角川文化振兴财团”是日本一家非常著名的出版公司,其创始人角川源义先生是有名的实业家兼诗人。角川财团先后设立了蛇芴奖·迢空奖、角川源义奖、角川财团学艺奖等多个奖项。角川财团学艺奖于2003年设立,授奖的对象是文学、文化领域里的既是典型的学院派研究成果又受普通读者欢迎的著作,每年从上一年度出版的作品中选拔、奖励一种或两种作品。前八届获奖作品都是有关日本历史、文学、民俗等方面的著作,我的《汉文与东亚训读文化圈》能获这个奖,自己也感到很意外。
段江丽 这说明您关于汉文与东亚训读文化的研究,不仅受到学界的高度肯定,也受到读者的普遍关注和欢迎,获得大奖,正是实至名归。
中日韩“三栖”学者
段江丽 您作为韩国人在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而且成绩卓著,在中日韩乃至整个国际汉学界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让人非常钦佩。您曾于2005-2009年,以外籍学者的身份任京都大学人文所所长,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您在日本学界的地位和影响。我想,很多读者都会和我一样,对您的求学经历及学术背景非常感兴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
金文京 好的。我之所以走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路,可以说直接受到吉川幸之郎先生的影响。我在高中阶段就拜读了吉川先生的“全集”,对中国文学、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于是,进入庆应义塾大学之后,毫不犹豫选择了文学部中文系;大学毕业之后,考入京都大学大学院,在田中谦二郎先生的指导下攻读中国文学专业的硕士学位。田中先生是吉川先生的弟子,所以,我就成了吉川先生的再传弟子。我考入京都大学时,吉川先生已经退休,但是,很幸运的是,我参加了吉川先生发起和主持的“读杜会”,有机会聆听吉川先生的教诲。所谓“读杜会”,就是专门研读杜甫的“读书会”。当时吉川先生主持的“读杜会”分两种,老师们参加的叫“大读杜会”,学生们参加的叫“小读杜会”。
我在硕士阶段的兴趣主要是经学和古典诗文,后来有机会去港台旅游,觉得吉川先生所说的中国,可以说是文人士大夫的中国,在此之外,还有不同的广阔的天地,于是兴趣慢慢转移到反映世俗生活的小说和戏曲上。
段江丽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个人的亲身经历对知识的养成乃至人生方向的选择都非常重要。您现在经常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中、日、韩三国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中日韩“三国”通,而您精通中日韩三国语言这一优势无疑是打通“三国”的有力武器。我注意到,您在京都大学除了给研究生开设专业课之外,还给本科生开设韩语的语言基础课。您生长在日本,日语不用说是您的“母语”;那么,您是否从小也一直坚持学习并使用韩语?是否可以说,韩语也与日语一样,是您的“母语”?
金文京 我在家里从小说的是韩语,因此,可以说有双重“母语”。其实,韩语和日语属于同一系统的语言,语法、语序有99%的相似度,韩语和日语中的汉字词汇有80%的相同,只是读音不同而已。在古代,韩、日在引入中国汉字时,最麻烦的是声调,所以,都放弃了声调,而韩、日两国的发音比较接近,韩国人和日本人在掌握了对方语言中三、五百汉字的读音之后,就比较容易猜出对方的话。这样说吧,北京话和广东话的差别也许比韩语和日语的差别更大。如果有心的话,学会了韩语或日语中的一种之后再学另一种其实很容易。
段江丽 作为习得的第二语言,您中文造诣之深实在让人惊讶和敬佩。听您讲课,看您用中文写的论文,乃至于邮件,用语地道典雅,古诗俗谚事典随手拈来,即使置身于中国学者群,也是佼佼者。您的《木鱼书目录·后记》中有一首早年游学香港大学时的感怀诗《冯平山图书馆最高楼晚眺》:“离乡两载事堪嗟,梦里频惊已到家。故国天涯烟波阔,神州山外夕阳斜。归期渐近情何怯,游兴方浓望转遐。最是春风难作别,登楼更看满城花。”您深厚的中文旧学功底于此可见一斑。能否请您简单谈谈,精通中日韩三国语言,对您的学术研究有哪些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金文京 如果说中日韩三国语言对我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的话,主要是能直接阅读相关材料。其实,与其说是影响,不如说是动机。小时候发现中、日汉字很多发音很相似,想进一步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是我选择学中文的一个重要动机。当初选中文系时,就是想要研究中国文学。而古代的日、韩,还包括越南等,其实都受到中国文学-文化的影响,同属于“东亚文学圈”,因此,我的研究也就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了日、韩文学-文化。
段江丽 关于“东亚文学圈”,稍后再向您具体请教。就我的感受而言,您因为精通中日韩语,对三国历史文化、世态人情、民族性格诸多方面都有深层的、细致入微的了解,所以,您的许多研究都体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微观处,深入中、日、韩,分析各自的特色;中观处,比较中、日、韩,指出彼此的联系与差异;宏观处,整合并超越中、日、韩,从“东亚”的视角立论,使问题上升到世界文明板块的高度。比如说,您在《高丽本〈孝行录〉与“二十四孝”》、《东亚近代知识人的一种形态》、《西湖在中日韩——略谈风景转移在东亚文学中的意义》、《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天下观与世界观》等代表性论文中,或多或少,都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金文京 要做国别之间的比较研究,直接通晓比较对象国的语言的确很重要。
段江丽 有趣的是,您以三种不同文字分别在中日韩三国出版的、影响很大的代表作《三国演义的世界》,第一章题目为“故事之始——‘三’”,竟然是从“《三国志》与‘三民主义’”相关的文人逸事、“事无三不成”的中国古谚以及“三”在中华文明中的特殊涵义等入题,引人入胜。我在网上看到一篇题为“日本人品三国——读金文京《三国志演义の世界》”的评论文章,特别说到您这个开头很有意思。
金文京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司马迁《史记·律书》说:“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等等,这些说法大家耳熟能详。其实,从音韵的角度来看,也很有意思。在古汉语的发音中,从一至十的十个数字中,只有“三”为平声,其余九个数字都是仄声,因此,如果要在数字中调节平仄,“三”出现的几率是百分之五十,独占半壁江山。所以,我认为,“三”多见于汉语表达,具有丰富的象征意味,原因之一就是声调上的特殊性。
段江丽 从声调的角度解释中国语言文化中“三”的特殊意义,的确非常新颖。套用中华文明中这个神奇的“三”字,您是地地道道的中日韩“三”栖学者,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巧合。
文献校注与团队研究
段江丽 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界,您主要以《三国演义》专家著称。您关于《三国演义》的系列论文、专著《三国演义的世界》,以及您与沈伯俊先生的题为《中国和日本:〈三国演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对话录”,都非常引人注目。2007年,您还和其他几位中日学者一起,出资购买了明万历刻本《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捐赠给中国国家图书馆,一时传为佳话。
不过,稍做了解就会发现,《三国演义》只是您研究的课题之一,事实上,您所涉猎的范围非常广。中国方面,您以通俗小说和戏曲为中心,广泛涉及到包括敦煌变文、日用类书、说唱文学、晚明山人活动等等在内的文学以及文化现象,甚至还会关注胡兰成、金庸等现当代作家。除此之外,您对日本的军纪文学、五山文学以及明治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杰出的教育家福泽谕吉的汉诗、东亚汉字文化圈的训读等等都很有研究,还撰写过不少中、日、韩语言学和翻译方面的论文和著作,您刚刚荣获大奖的就是东亚语言文化方面的著作。可以说,您的研究是以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和戏曲为中心,广泛涉及到中日韩三国语言、文学、文化以及彼此之间的比较。我觉得,要做归纳的话,您的研究是以文学为中心,从文献校注、文本细读以及文化分析三个面向展开。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对文献研究的看法以及您所从事的文献研究工作。
金文京 文献整理、校勘是研究工作的基础,这一点是大家的共识,不必多说。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正确、精良的底本,后续的研究当然就得大打折扣。其实,三十多年来,我的研究工作尽管涉及到了许多领域、许多作家,但是,我主要做的、一以贯之的工作其实是文献研究,具体来说包括文献本身的整理和校注两个部分。前者做得不多,只是与朋友合编了《广东说唱文学研究——木鱼书目录》,并与中国学者黄仕忠、日本学者乔秀岩合编了《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第1辑),我更多、更主要的工作是文献校注。
段江丽 我们首先谈谈木鱼书吧。木鱼书作为广州方言区的民间讲唱文学,从晚明到民初,曾有大量刊刻本问世,目前在国际汉学界很受重视,甚至被称为“农耕社会底层艺术的化石”。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关注的人却很少。从中国期刊网上以“木鱼书”、“木鱼歌”为主题词进行搜索,20世纪80、90年代,相关论文寥寥无几,至今不过73篇,其中57篇发表于2000年以后。不过,这一数字也说明,木鱼书正逐渐走进中国学者的视野。请您谈谈《木鱼书目录》以及相关研究情况。
金文京 我对木鱼书的关注,源于偶然的机缘。1986-1988年期间,我申请到当时我所供职的庆应义塾大学的资助,前往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游学两年。1987年1月,在港大的冯平山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木鱼书。当时,我正与几个朋友一起在研究《花关索传》。看到木鱼书,觉得它与《花关索传》之类的说唱词话是同类的东西,于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想方设法查找、阅读木鱼书,并读到了梁培炽先生的《香港大学所藏木鱼书叙录与研究》。在新加坡,在辜美高先生的建议和帮助下,我曾前往马来西亚参观,在马来西亚图书馆也看到了木鱼书。当时听说广州中山大学也藏有木鱼书,很想去看,但是由于韩中之间尚未建交,很遗憾未能成行。后来,我在《花关索传研究》注释中引用了木鱼书的一些材料。
回到日本之后,我还是一直忘不了木鱼书。有一天忽然接到香港中文大学黄耀堃先生的电话,说香港有木鱼书在卖,但是买的人不多。我现在藏有的木鱼书大部分都是那时侯通过黄先生购买的,他还给我寄来了香港中文大学吴瑞卿女士的博士论文《广府说话唱本木鱼书的研究》复印件。这样,我又重新与木鱼书结缘,并发表了论文《香港的传统艺术——木鱼书》。此后,我在古屋昭弘先生的建议和帮助下,与稻叶明子、渡边浩司等朋友们一起着手调查和研究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等机构馆藏的木鱼书。后来,在许多学界朋友的帮助下,调查范围也不断扩大。最后,《木鱼书目录》共收录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日本、马来西亚、法国、俄罗斯等各地馆藏木鱼书3874种。正如你刚才提到的,在我们编写《目录》的时候,有关木鱼书的研究还不多,除了前面提到的梁培炽先生的著作和吴瑞卿女士的博士论文,还有谭正璧、谭寻两位先生的《木鱼歌潮州歌叙录》也是我们参考的重要著作。在我们的《木鱼书目录》出版时,日本研究木鱼书的唯一先驱波多野太郎先生欣然赐序,我和稻叶明子、渡边浩司各写的一篇介绍性文章,这些都附在书的前面。通过它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当时木鱼书的研究情况。
段江丽 您因为偶然的机缘,用心坚持,竟然取得了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真是令人羡慕又钦佩。那么,《木鱼书目录》与谭氏《叙录》比,有什么特点?
金文京 简单地说,我们的《目录》有两个特点:第一,所收书目更为详备;第二,在具体的论述中,我们还涉及到了木鱼书与敦煌变文的关系。
段江丽 这样,也就可能启发更多新的学术增长点,对中国研究木鱼书乃至整个说唱文学的学者来说,这部《木鱼书目录》应该很有参考价值,相信它会越来越受到关注。关于《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从黄仕忠先生的《出版前言》中可知,这套丛书是在全面调查、检核的基础上,准备从日本所藏的明刻、旧钞戏曲作品中选择孤本及稀见本八十余种分卷予以影印出版,这套丛书对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里程碑式的意义不言而喻。与目录编撰和整理影印古籍相比较,文献校注无疑难度更大。
金文京 二、三十年来,我在文献校注方面的确付出了一些努力,也乐在其
中。我主要做的有以下几项:《花关索传研究》, 于1989年由汲古書院出版;《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校注》,于1992年刊于庆应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4号;《〈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研究》,于1998年由汲古書院出版;《〈老乞大〉:朝鲜中世纪の中国语会话读本》,于2002年由平凡社出版;《邯郸梦记校注》,于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至正条格〉校注本》,于2007年由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出版;《新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由汲古書院陆续出版,目前已出版的有《元刊杂剧的研究(一)——〈三夺槊〉〈气英布〉〈西蜀梦〉〈单刀会〉》(2007年)、《元刊杂剧的研究(二)——〈贬夜郎〉〈介之推〉》(2011年),这项工作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把元刊杂剧三十种做完。这里面,除了《〈王昭君变文〉校注》之外,其他几种都是与朋友合作完成的。
段江丽 有个细节我很好奇:在日本,合著的著作署名一般按什么原则排序?怎样体现参与者的个人成就?
金文京 一般按姓氏假名排序。至于每个人所作的工作,大家根据自己的专长,各抒己见。经过讨论,再择善而定。
与朋友合著的《花关索传研究》是我的第一部著作。众所周知,研究古代文献,校勘、校注非常重要。我们在长期的校注工作中,还特别强调一点:以往的校勘学在比较不同版本的文字之后一般只需要判断是非对错,选择对的、正确的文字作为善本就算完成了任务,我们则强调,错字也值得研究:错字产生的原因、错字是否会产生影响或者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也值得研究。
段江丽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一般的校勘,对错字——也就是传写和翻刻中出现的“误文”,只需要分析原因、做出对与错的判断,而您和您的同仁们在校注过程中,除了分析“误文”产生的原因之外,还会进一步研究“误文”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产生的影响?
金文京 是的,我们很强调这一点。从这个角度,往往会有新的收获。我们的校注,不是以一般读者为对象,而是以专家为对象。我在对《王昭君变文》做“校注”时,就校出了一些中国学者没有发现的问题。至于合作的项目,我们在进行校注工作时,对每一部作品、每一句话乃至每一个字,都希望能够集思广益、精益求精。以前中国人做校勘,大都是个人独立去做,当然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个人的时间、精力、学识总是有限的,总有遗漏的地方。各方面的专家坐在一起,大家互相切磋、辩论,能解决很多问题,也能减少错误的几率。再回到《花关索传》的话题。1967年在上海市西北嘉定县出土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传》(简称《花关索传》),刚出土时,很乱,博物馆进行了整修,才勉强像一本书。到目前为止,中国学界只有朱一玄先生的校点本。我们在研究《花关索传》时,每星期一次,每次5、6个小时,大家坐在一起,一字一句读,这样持续了三年。
段江丽 《花关索传》及相关研究在中国学界似乎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金文京 我们的《花关索传研究》其实是用中文做的注,在中国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我想主要有这样两点:第一,1980年代中日之间的学术交流还不象现在这样方便;更重要的是第二点,中国主流学界似乎对《花关索传》兴趣不大、评价不高。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花关索传》与云南、广西、贵州等地的傩戏有很多相似之处。我在1990年代曾应邀前往中国大陆参加过傩戏方面的研讨会,由文化局等政府部门主办,与会者多是地方演出剧团以及文化系统的人,很少有学院派学者,而且大家讨论的也主要是表演艺术方面,很少涉及主题、宗教等方面的内容。据我了解,对傩戏的性质,中国大陆学界也有过争论,有的认为应该纳入中国戏曲史主流,大多数人不同意;也有的认为傩戏只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戏曲形式,可是后来发现一些汉族集中居住的地方也有,又说只是边缘性的戏曲,结果不了了之。根据我们的研究,《花关索传》对梳理、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史是非常珍贵的资料。这一点稍后有机会再谈。这里,我们还是接着说文献校注的话题。
段江丽 好的。您与李晓先生合注的《邯郸梦记校注》内容包括字音、词义、本事、出处等,尤其将典故、方言俗语、借用或者化用前人诗词以及难解的词语等作为注释的重点,可以说,这一校注本反映了当时关于《邯郸梦记》研究的前沿成果。我发现,在文献整理中尽量体现前沿性研究成果,是您和您的同仁一贯的追求。
金文京 是的。我和李晓先生一起做《邯郸梦记校注》的情形也与《花关索传》研究情况大同小异。当时李晓先生来京都大学做一年的研究学者,我们几乎每星期都有一、两天坐在一起,那时刚刚有了“四库全书”电子版,我们一边讨论,一边在电脑上检索。正好日本立命馆大学发现了一部在中国国内已经失传的万历刊本《邯郸梦》,我还写了一篇文章附在后面。从开始校注到最后出版,这本书先后打磨了四年。
文献校注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当然也需要关注既有研究成果。尤其我们在为日本学界提供中国古籍文本时,还有翻译的问题。要有正确的底本才可能有正确的译本,所以,首先要参考各种研究成果,对底本有尽可能正确的了解。我们对董西厢的研究,也持续了四、五年,《〈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研究》包括解说篇、本文篇、曲谱、语汇索引等四个部分,其中“解说”部分为日文,“本文”包括中文和日译两部分,曲谱和语汇为中文,可以说提供了文本校注、日文翻译以及相关研究等综合性的成果。其实,这本书是我们几位同仁在田中谦二先生长年研究的基础之上共同努力的结果,出版社评价它是关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最新、最好的研究书”,虽是溢美,但的确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段江丽 据我了解,董西厢目前在中国大陆的研究也很不充分,作为研究基础的文献整理也还有待加强,好像只有凌景埏先生校注的《董解元西厢记》(1962年初版)以及朱平楚先生的白话文译本《西厢记诸宫调注释》(1982年版),都属于通俗类读物。《〈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研究》如果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一定很有意义。
金文京 我们尚未与大陆出版界联系过此事,看机缘吧。
段江丽 到目前为止,在您的研究中,持续时间最久的应该是“元刊杂剧三十种”吧?
金文京 不错。1987年,我的老师田中谦二先生退休之后,循京大的传统,自己在家里开设了“读曲会”,继续给我们讲课。后来,田中先生80岁高龄时对我们说,“该教的都教了”,不再主持“读曲会”了,我们几个受业学生决定将老师的“读曲会”继续下去,直至现在。在日本,私下里的“研究会”、“读书会”不少,但是,像我们这个“读曲会”坚持了近30年的则不多见。
我们“读曲会”研读的主要对象就是“元刊杂剧三十种”。众所周知,《元曲选》与其说是经过臧懋循全面校订还不如说是由他改编而成的。因此,以《元曲选》来考察元杂剧的形态乃至元代的语言,其可信性都要大打折扣。相对来说,“元刊杂剧三十种”虽然有不少错字、脱字、假借字,但是,它们却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元刊杂剧”的本来面貌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因此,把版本粗糙、内容难解乃至难以充分利用的“元刊杂剧”进行整理、校注,使其能够更好地被广大学者利用,是一项虽然艰难却非常重要的工作。
段江丽 您在前面提到硕士阶段曾参加“小读杜会”,这一经历甚至影响到了您一生的职业选择。其实,很多来日本访学和研究的中国学者都对日本学术界的“读书会”印象深刻,不少人回国之后,不仅身体力行、与周边的同事和学生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共同研究,还撰文介绍、推广,比如说,曾在京大文学部做JSPS项目研究学者的杨合林教授在《日本中国学研究之观感》一文中就将“读书会”作为“传承和坚守学术传统的一种重要方式”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金文京 其实,“读书会”主要是京都大学的传统,在日本其他大学包括东京大学不一定有这种形式。我们“读曲会”的研究成果先后在日本《佐贺大学教养部学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报》及《人文》等杂志上陆续刊载,最后再以《元刊杂剧的研究》系列著作的形式出版。这些著作的基本体例是:首先,对每一种杂剧的作者、内容、同类题材作品以及该杂剧在明以后的发展等情况进行介绍;然后,逐段对原文本进行校注并翻译为日语。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校注参考了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台北,1962)、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北京,1980)、宁希元《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兰州,1988)三种既有校注本。这三种著作都有自己的长处,但是,也都有不足。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徐本未能参考郑本,宁本虽然参考了前两种,有些论断也还值得商榷。我们尽可能采三家之长,对未能判断是非的事例则只是对不同说法做大致的翻译、解说,并在注中提示有另说可通。此外,我们还编写了配套的《元刊杂剧三十种语汇集成》以作参考。
段江丽 我拜读过您惠借给我的《元刊杂剧的研究(二)》。这部著作不仅为《贬夜郎》、《介子推》两种元刊杂剧提供了精良的校勘,而且通过“解说”与“注”,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相关材料和研究成果,可以说,无论版本还是论述,都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从1997年的读曲会,到2007年出版《元刊杂剧的研究(一)》,过了整整20年;到2011年出版《元刊杂剧的研究(二)》,已经24年;等三十种全部出齐,肯定还要若干年。这样,由一个团队长时间精益求精打磨出来的成果,一定是可以藏之名山、传之久远的利“剑”、宝“剑”。据了解,《元刊杂剧的研究(一)》是由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出版的,请问整套《元刊杂剧的研究》的出版都是如此吗?在日本,类似于这样的学术资助在时间上一般有什么要求?
金文京 振兴会只资助了第一本,第二本我们也申请了,但未能成功。其实,全世界的情况可能都差不多,政府对文科的资助远远不如理工科,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对学术著作的资助似乎越来越少了。第二本最后是由我们大家出资出版的,不过问题不大,大家都承受得起。
段江丽 包括师生在内的学术团队长期、认真地研究同一课题,乃至同一文本,的确是出学术精品的有效方式,这种方法很值得中国学界借鉴。目前在中国,政府对学术的资助力度其实在逐渐加大,这无疑有利于学术事业的繁荣。遗憾的是,有些资助项目成果出来之后,质量很成问题,粗制滥造者并不少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各级项目管理机构往往要求短时间内结项,而且强调项目和成果的现实功用性,这种急功近利的规定,不利于学术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违学术的规律。
金文京 在日本其实也同样有这个问题。拿了项目,有结项的压力,而文科研究,很多时候要靠长期积累。所以,拿了项目、有经济资助虽然是好事,但是,在研究中并不自由。研究的最佳状态应该是,不要政府的资助,没有时间的限制,自由自在,大家由于相同的兴趣、爱好坐在一起,认真阅读、深入钻研。
段江丽 所以,有人说,真正的学术是贵族化的、有钱有闲阶层的精神产品。在您参与校注的重要文献中还有两部,《〈老乞大〉:朝鲜中世纪的中国语会话读本》和《〈至正条格〉校注本》,都与中韩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有关。请您介绍一下这两部著作。
金文京 《老乞大》和大家比较熟悉的《朴通事谚解》都是朝鲜高丽朝的汉语教材。据有关材料,《老乞大》、《朴通事》在1423年正式铸字出版,此前已经被列为司译院的考试科目,而《老乞大》的编纂时间大概在高丽忠穆王二年(1346)后不久。这两部书中都保留了大量元代的语言和民俗资料,《朴通事谚解》因为其中有关于《西游记平话》的材料而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研究界熟知,《老乞大》则被很多语言学研究者关注,文学界较少关注。传世的《老乞大》有纯汉语本、蒙语本、满语本和谚解本。所谓“谚解”是指朝鲜李朝的汉学家用“谚文”所做的注音、疏解,“谚文”是李朝世宗二十五年(1443)创制的拼音文字,也就是今日朝鲜文仍在
- ·世界汉学讲坛 | 何广思教授解读中拉
- ·阿根廷何广思:超越西方范本才能获
- ·阿尤布: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
- ·黄卓越:早期中国的书写与汉学研究
- ·薪火永相传,著名汉学家马克林讲汉
- ·《人民日报》:《用翻译架起中葡文
- ·蔡宗齐(美国):开辟中国文化走向
11 月 22 日下午,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北京语言大学主办、世界汉学中心承办的世界汉学讲坛第九讲成功举办。本次讲坛由...
10 月 18 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
日前,由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牵头建设的土耳其汉学家理事会在青岛正式成立,土耳其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土耳其著...
摘要:该文原为作者2021年10月20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举办的一带一路汉学研究论坛上所做的现场演讲,对海外汉...
2023年6月7日下午,薪火永相传大师说汉学暨世界汉学讲坛第四讲成功举办。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
2023年02月0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7版刊登了《用翻译架起中葡文化交流的桥梁》一文。文章由新汉学计划海外高级中...
天下学问一家: 开辟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新路径 蔡宗齐 蔡宗齐(Zong-qiCai),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校区东亚语言文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