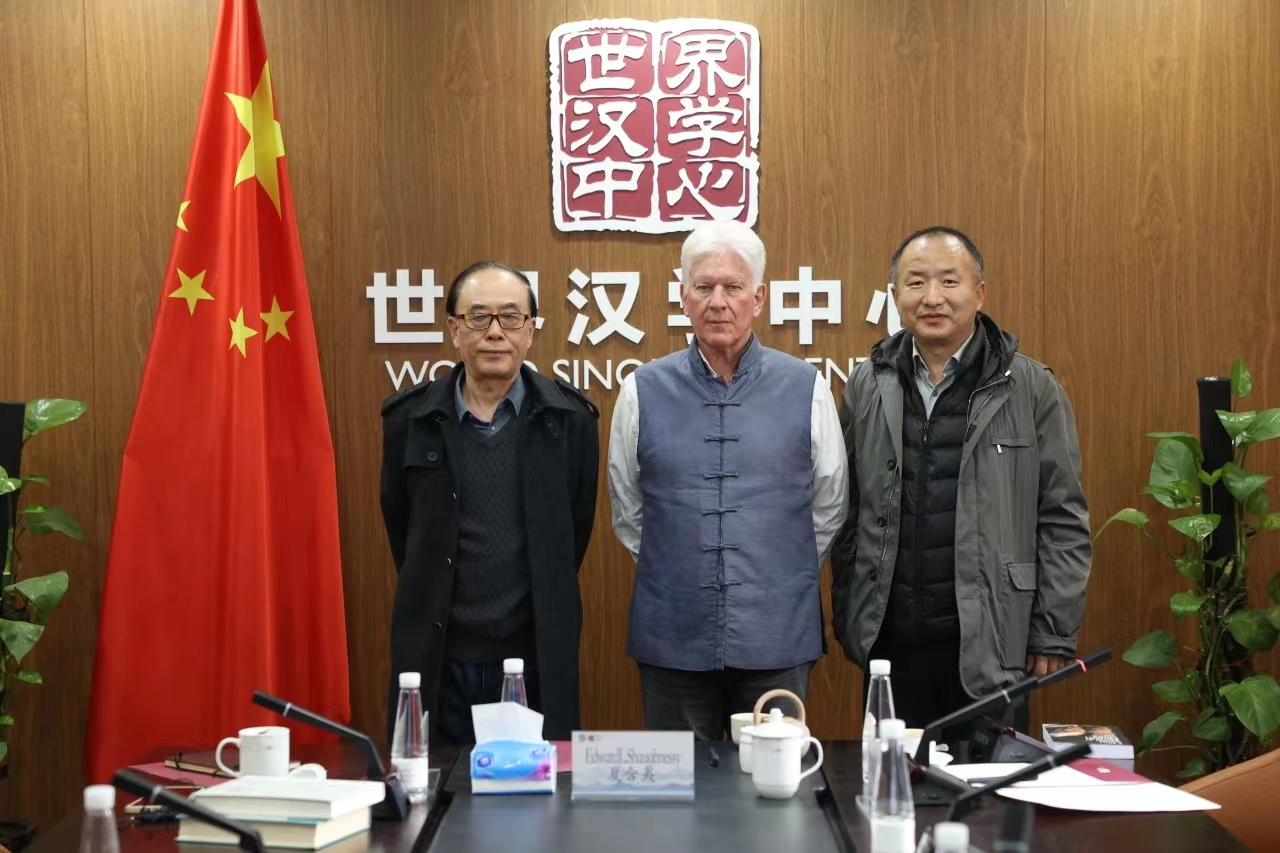苗壮:明代出使朝鮮使臣的域外記志詩
苗狀
明代出使朝鮮使臣的域外記志詩[①],是指由明帝国官方派往朝鮮的使臣作家群在奉使朝鮮的政治活動中所創作的文學文本的總稱,在文體上以詩歌為主,同時還包括了少量的文和詞。有明一代,出使朝鮮的文官使臣在奉使活動中形成了較為固定的書寫慣則,留下了為數眾多的此類文本。目前,國內學界已有部分學者有意識地對域外記志詩的版本給以細緻地考辨並在此基礎上對其文學價值給以適當地評估[②]。但是就此類研究普遍使用的理論工具來看,仍是以較為單一的文學理論框架下諸如創作論、風格論、價值論等以文本本身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範疇,客觀上造成了對文本與作者身份關係的忽視或疏離。而在這些域外記志詩的研究中,對作者身份的關注是至關重要的。闊而言之,使臣作家們特殊的奉使身份及其必然參與的外交活動是域外記志詩誕生的直接語境,使得此類文本不能完全等同于明帝国疆域內文人的自由寫作。使臣的文學敍述是在明帝國與朝鮮的朝貢關係[③]的特定語境中創作的,由此使臣的域外記志詩已不單純是文學審美化的書寫,而當進一步視為使臣身份向文學/文化層面的延拓。由此,本文將使臣身份作為解析域外記志詩的關鍵,並試圖在此基礎上,對域外記志詩給以恰當的定位。
一、使臣身份觀照下的域外記志詩
如前所述,奉使朝鮮使臣的域外記志詩與明帝國域內的文人寫作並不完全相同的主要原因在於使臣的特殊身份。從有明一代奉使朝鮮使臣的統計來看(見附表),使臣可以分為文官、武官和宦官,其中文官使臣是域外紀事詩的主要創作者,其特殊的作家身份与明帝國無法分開審看。
首先,就文官使臣職務而言,他們大多數都是來自明帝國翰林院、六科、行人司的中央官員。在這三個部門中,除了行人司“專職奉使”等職能相對單一之外,按照明代官方文獻的記述,翰林院和六科在帝國整個行政系統中處於核心地位,翰林院和六科的朝廷文職官員即是國家最高行政機構的負責人。在這一群體中選拔出的奉使官員,在出使朝鮮之前已經直接參與到帝國的最高行政工作之中。[④]如天順四年(1460)出使朝鮮的正使張寧,在奉使前任禮科給事中,其間“六科章奏多出其手,每有大議必問張給事云何……其才略為一時所稱。”[⑤]隆慶元年(1567)正使許國時為翰林院檢討,先後“在密勿樞機之地者三十年”[⑥]。由此不難看出,使臣本身即是國家政治的共預者和決策者,對帝國的政治權威亦懷有認同感和歸屬感。這種認同感和歸屬感散見於使臣日常行文中,不勝枚舉。甚至使臣在其政治生活陷入低谷時仍然保持著這種態度,由此可見一斑。如景泰元年(1450)出使朝鮮的正使倪謙曾被貶謫到宣城,嘗與“二三遷客”唱詩游宴,倪謙卻將貶謫中的詩文創作視為“聖德之賜”,並認為“是詩偶為好事者所傳,四方之人有以想見邊亭塞垣,人心暇豫有如此者,豈不益驗國家太平之盛也哉?”[⑦]雖然到了明代中後期,出現了諸如隨著台閣權威的喪失,翰林院和六科的文職官員對國家主義的認同感明顯弱化、六科文職官員在實際工作中同文字書寫相疏離等一系列新變,但是明帝國與朝鮮王朝的朝貢關係並未受此影響,並且由於使臣的域外記志詩寫作已經形成了一種相對固定的寫作慣例(有些學者稱之為“《皇華集》的傳統”),故而在域外記志詩中對國家主義的認同感基本是始終如一的[⑧]。
其二,就文官使臣的文化修養來看,幾乎所有來自翰林院、六科乃至行人司的使臣,都是從帝國全國性的考試中脫穎而出的獲勝者,在長期的學習中獲得了良好的文辭修養和文字書寫能力,並在日常生活中參與到詩文的寫作和彼此唱和之中。如成化十二年(1476)使朝正使祁順,嘗與陳獻章、彭紹、楊一清、司馬垔、周孟中、丘霽、蕭顯、何文縉、陳綺、王臣、羅善等彼此寄詩唱和;又在任江西參政期間“會即隨事唱酬,篇章交錯;別亦馳緘往復,如元白之為。期月間又得詩共二百餘首”[⑨],此事雖在祁順出使朝鮮稍後,時間上略有參差,猶可窺見當時文臣群體交接的局面。又如景泰元年(1450)正使倪謙與茶陵派領袖李東陽“為同年,交最深”,李東陽為其文集作序,將倪謙視為繼宋濂、楊士奇、劉定之之後的又一文壇巨擘。[⑩]而就倪謙個人文才而言,《四庫提要》稱“體近三楊而未染其末流之失,雖不及李東陽籠罩一時,而有質有文,亦彬然自成一家矣。”[⑪]
由以上的敍述可知,使臣在明帝國內已經具備了政治和文化的雙重身份,當這種雙重身份共同扭結在文官使臣身上之時,兩者之間勢必會造成相互的滲透。比方說文官使臣已有意識地將國家、王教、世功等政治意象視為詩文存在的必要性因素,並導致了政治性話語對詩文創作觀念的直接浸入,這一點表現地非常明顯。如倪謙從文學作用論的角度認為,“非載夫道其文不能行遠……蓋文運與世運相關,文章之盛者,世道之盛也。”[⑫]將文章創作與世運之興衰相聯繫,把個性化書寫納入到國家主義的框架之中;張寧亦從文學發生論的角度認為,“聖賢之文,原於性情、蘊蓄為道德、著見為功業。”[⑬]將詩文寫作理解為由性情、道德、功業由內向外延展的生成方式,其最終的落腳點是國家的政治功用,這使原本自由的文學寫作和文學價值歸入政治實踐的維度。此類文章功用論的觀念,為使臣在出使過程中政治身份向文化身份的延展提供了詩學理論上的依據和具體言說的支持。[⑭]
鑒於使臣上述兩種身份特徵,可以大致將使臣的全部域外記志詩依此劃分為使事詩文和紀行詩文兩類。簡而言之,使事詩文即與出使政治性任務直接相關的詩文。它往往是政治實踐過程中使臣對出使情況的敍述,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出使活動的附屬產物。由於在出使活動中,朝鮮官廳往往遴選朝鮮文臣與使臣左右相伴,某些詩文創作產生於對話性場域之中,帶有彼此唱和的性質[⑮],因此這類詩文受到場景限制較多,創作自由度相對狹窄。紀行詩文則是指記錄沿途山川風物等日常化寫作詩文,它並不受到對話性場域的直接限定,同出使任務在一定程度上亦有疏離,在表述上更接近文人日常性書寫,創作自由度也相對寬鬆。雖然兩類詩文只是粗線條的劃分,並且兩者間在某些題材上偶有交涉,但總體來看其類屬的基本框架仍較為明晰。兩類詩文基本可以涵蓋使臣全部的域外記志詩作,就所占比重而言,兩者幾乎各占一半,數量也基本持平。
(一)、使事詩文
按照朝鮮禮儀接洽制度的規定,朝鮮官廳在得知使臣從北京出發的消息之後,即“遣遠接使於義州、宣慰使于五處迎送宴慰。”[⑯]當使臣渡過鴨綠江與遠接使會面,兩國進入到正式的使事接洽之中。使事詩文,即是指使臣與朝鮮官廳接洽中,一系列政治活動安排間使臣所創作的詩文。
從明帝國使臣和朝鮮官廳對這些使事活動的認知可以看到兩層意思:首先,從帝國使臣的角度而言,使臣是帝國權威在異域發生效力的直接觀察者,朝鮮君臣是否具備誠敬恭順的態度,都要通過此類“邦交之儀”、“使事交際之儀” [⑰]等加以品評。其二,對於朝鮮官廳而言,使臣的到來除了具體的政治任務之外,尤是朝鮮展現自身禮儀和文化在“外夷”序列中優勢地位的時機。故而,朝鮮國王有意地安排“能文之士”接洽陪宴[⑱]。所謂的能文之士,主要是指朝鮮弘文館、藝文館、成均館、春秋館和承文院等機構的高級文職官員。按照朝鮮《經國大典》的記述,弘文館、藝文館、成均館、春秋館和承文院均為正三品衙門,且均與文辭工作有關[⑲]。由於朝鮮王朝以儒治主義立國並以漢字作為政府工作文字,因此這些朝鮮高級文職官員與明帝國的使臣一樣,具有良好的漢字書寫能力以及豐富的漢文化知識,他們構成了同使臣唱和的另一方。這樣的安排試圖營造出帝國內文人彼此之間日常交接相似的文化氛圍,其實質亦在追求文化認同背後所交揉的帝國對朝鮮“不以夷狄視之”的政治褒義之認可,使事詩文正是在使臣與朝鮮官廳的雙重政治期望下誕生的文本。
使事詩文中雖也有政治描述較為淡化、試圖展現出日常性文學創作風貌的文本,但是其總體數量較顯單薄,且政治因素偶爾穿插其中,政治敍述在此類詩文中仍佔據主導性地位。在這些直接政治性敍述的詩文中,有兩個主題較為突出,其一是對帝國君主恩澤廣溥的歌詠;其二是對朝鮮欲尋求的東亞政治與文化地位的肯定或褒獎。
就溥揚君德的主題來看,如前所述,頌揚帝國君主的權威是使臣出使前已有之特徵,它最直接的來源即是使臣對帝國權威在心理上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在出使過程中得以進一步強化其原因有二。首先,是在出使之時,使臣被賜予一品麒麟服,獲得了奉詔敕而行的權力,使臣成為帝國政治權力向異域延展的直接行動者,這種安排致使使臣的政治身份進一步向帝國權威的靠近。[⑳]就使臣其個人而言,他往往會將出使的具體任務視為溝通個人同帝國關係的直接行為,進而將關係的重心完全放置在帝國一方,並且在出使的日常敍述中廣泛表述。如“使臣忝竊承王命,不惜千峰與萬峰”[21](張承憲《朝鮮往返即事感懷共八首》)、“長安萬里家何在,王事悠悠未敢安”[22](同上)、“四序頻更催我老,一官常自為君憂”[23](陳三謨《高平道中》)等等,進而將自身同帝國權威綁縛在一處;其次,朝鮮官廳在使臣到來後,在禮儀和文化上極盡展示自身同明帝國文化的相似性,這在使臣看來,帝國的禮樂文化已經遠播“外夷”,並邏輯地將其視為是帝國聖化的產物,如“文風豈特覃東海,聖化於今遍八荒”[24](倪謙《謁文廟》)、“聖朝德化天無外,喜見殊方重禮儀”[25](祁順《宴義順館》)、“最喜聖朝聲教遠,殊方持節得徘徊”[26](張謹《和徐參贊詩韻》)、“聖代文風遠,賢藩禮數優。車書昭一統,儀典軼諸州”[27](龔用卿《至寶山間》)、“朝廷禮樂洽遐方,龍章普照咸歸王。一方奔走歡聲洽,老幼聚觀如堵牆。君不聞,盛明大度同八荒,山東聽詔邁漢皇”[28](龔用卿《入漢城喜晴賦》)、“聖世文教洽四方,皇極敷言駕百王。念而箕疇素秉禮,特示優遇崇垣牆。君不見,聖敬日躋無怠荒,明見萬里陋漢皇”[29](吳希孟《入漢城喜晴次雲岡韻》),此類描述比比皆是。讚頌帝國君主恩澤廣溥成為使臣使事詩文中的第一個主題,並同使臣的出使目的——驗證帝國權威在異域的效力達成了一致。
對朝鮮政治與文化地位之肯定或褒獎,可以視為是前一主題向朝鮮一方的進一步延展。作為恩澤流布的異域國家,朝鮮因其展示的恭順態度獲得了使臣及其所代表的帝國之認可,從而也肯定了兩國間朝貢關係的繼續存在。在此類詩文中,東藩、屏翰、箕子等有關朝鮮的意象在使臣筆下廣泛出現,如“國王知感聖恩深,玉帛梯航匪自今。常願東藩為屏翰,賢哉忠孝一生心”[30](陳鑒《國王臨別特書“感皇恩莫相忘”六字,見遺片言之間而君臣之義、友愛之情,藹然可見,因賦二絕以答盛意》)“忠勤一念思無斁,永固箕封久版圖”[31](祁順《無題》)、“偉哉東國此賢王,道率群臣入憲章。一代儀文周典禮,百年文物漢衣裳”[32](張謹《無題》)、“握符久已鎮東藩,忠孝承家作屏翰。國度尚存周禮樂,人文猶守漢衣冠”[33](龔用卿《贈國王》)等等。帝國東亞的政治秩序和自身禮樂文化向異域延展的事實被反復地描述,這也同朝鮮官廳的政治訴求達成了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使事詩文往往有朝鮮文臣參與唱和,這既是一種政治上的必要安排,又是文化上的自我展示,進而在詩文創作過程中形成了一種交互性的言說場域。這種言說場域產生了兩種作用,其一,明帝國的使臣往往只有正副二人寫作詩文,而朝鮮參與唱和的文臣則有幾人乃至十幾人。明使一人賦詩,朝鮮文臣數人吟詠,這樣就導致了朝鮮文臣在某些唱和詩文的數量上遠遠超過了使臣的創作,彰顯了朝鮮自身的文化之盛。其二,朝鮮文臣的唱和一般是繼使臣賦詩後對同一主題的吟詠,這就促使了使臣吟詠的兩大主題通過交互性的言說方式得以鞏固和加強。就使臣的詩文創作而言,原本已被政治浸染的使事詩文在這種場域中被進一步政治化。
(二)、紀行詩文
紀行詩文,是使臣出使過程中描述沿途山川風物以抒寫個人情感的文本,從總體上看,這些詩文雖為出使沿途之作,但是它更接近文人的日常化寫作,帶有明顯個人書寫的色彩,同使事詩文相比也展現出如下幾個異樣的特點。
首先,紀行詩文與政治事件的關係淡弱。雖然出使任務為紀行詩文的創作提供了條件,但就紀行詩文產生的直接語境來看,在使臣尚未同朝鮮官廳接洽時,此類詩文的創作就已經開始了。按照雙方儀制的規定,朝鮮官廳的政治接洽在使臣到達鴨綠江邊、東渡進入朝鮮境內正式開始,但是使臣離開明帝國的京師後就已經開始了紀行詩文的創作。僅以天啟元年(1621)出使朝鮮正使劉鴻訓沿途行次所吟詠的詩題為例,自離開京師始,劉鴻訓依次吟詠的詩題有《辛酉二月奉使朝鮮出都》、《潞水曲》、《鼎居歌薊門道中》、《曉發薊州》、《玉田三首》、《榛子城中歌》、《遷安里二首》、《七家嶺東發》、《憇安省墩》、《永平三日歌》、《初望海志喜》、《撫寧東下五首》、《高嶺驛偶成》、《寧遠浴湯泉》、《十三山》、《廣寧南風中逢葉問羲戶部》、《摩多樓子》、《醫巫閭四首》、《沙嶺昧爽》、《三岔河》、《入海州境喜賦》、《鞍山道中五首》、《遼城放歌行》、《遼陽東趨》、《青石嶺》、《小石門奉朝鮮使》、《甜水堡雨雪三日》、《上巳日霽趨通遠》、《鳳凰城望南山》、《三月十日渡鴨綠江》等等。[34]這沿途一月紀行詩文的創作並沒有朝鮮文臣隨之唱和,也並不涉及到兩國接洽的問題,出使的政治性因素對詩文創作的干預明顯淡弱。在使臣進入朝鮮境後,由於朝鮮文臣的遠迎使相伴同行或同使臣唱和,紀行詩文才受到政治活動的直接涉入,創作的自由度也逐步受到限制,並隨著向漢城的日益行進,這種政治的涉入越發強烈,以致諸如謁文廟、謁箕子廟(墓)、漢江遊宴等題材已很難再劃入紀行詩文的範疇,而更多地帶有了政治言說的色彩[35]。不過就紀行詩文的整體創作來看,其未受政治直接浸染的詩作數量仍占主要部分,故而紀行詩文仍可作為文人日常性書寫同使事詩文區別開來。
其次,紀行詩文在總體上並未受到直接政治事件的干涉,故而其吟詠的題材也較使事詩文更為多樣化。
其一,沿途風物的描繪是紀行詩文中最為主要的題材之一。有明一代,除了部分使臣因遼東地方戰亂而被迫從海路到達朝鮮之外,大多數使臣仍是通過遼東貢道奉使朝鮮。在使臣的認知中,遼東是“夷夏之所交也”,在那裏“山川異制,風土異宜,民性不同,政因俗革,天下皆然莫之概也。”[36]至於朝鮮更是域外之地,所以對於沿途風物的描寫最多,從京師直到漢城,每處驛站、館所、名勝古跡幾乎都有使臣吟詠。今信取數首以觀其大略:
江水日夜流,江色淨於碧。無數渡江人,臨江候潮汐。[37](張承憲《大同江》)
一曲溪流古渡遙,長松百丈架新橋。林花野草隨波出,香氣渾如百和椒。[38](薛廷寵《豬灘》)
晚潮獨上彩鷁船,兩岸燈聲雜棹傳。白鶴歸林鮫室靜,風濤不見暗籠煙。[39](歐希稷《夜泛大同江用高太常韻》)
東林古城草徑斜,壞垣崩石頹泥沙。山深地僻人不到,開遍東風幾度花。[40](龔用卿《東林古城》)
其二,前現代時期由於交通不便,在帝國的文學統序中描述路途的艱辛已經成為固定的歌詠題材,在明代出使朝鮮使臣的域外記志詩中此類題材同樣也廣泛出現。如倪謙過盤道嶺“石路崎嶇曆五盤,始從山麓到山端”[41](倪謙《盤道嶺》),過高嶺“緣崖若魚貫,屈曲勞攀躋。上合千尺松,下臨萬仞谿。藤梢射我眼,棘刺鉤人衣。嚴寒冰雪深,十步九滑蹄。”[42](倪謙《陟高嶺》)劉鴻訓在《上巳日霽趨通遠》也說“車下僕人殊可憐,泥途蹇足踏春田。不知田中更浮淖,車前已踣後仍效”[43]等等。
其三,使臣從京師到達朝鮮漢城再折回,往往歷時數月,帝國文學統序中的另一題材——異鄉離愁,同樣也相當顯著地見諸於使臣的紀行詩文之中。如:
昨夜漫天雨雪飛,曉來寒氣逼人衣。軺車又向雲興去,千里家山何日歸。 [44](張謹《曉發林畔館》)
黃金臺上袂初分,回首燕山已暮雲。明月何時重對酒,青山終日倍思君。深村斜日平蕪靜,旅抵西風落葉紛。我有孤懷何處寫,燈前愁誦楚騷文。[45](陳三謨《懷省中諸僚友》)
此外,詩文題贊、讀書心得等都是使臣紀行詩文中常見的題材。縱觀這些紀行詩文,可以看出,諸如皇恩、盛德、綸音、帝澤等與出使直接任務有關的政治意象並未深入其中,詩歌的日常生活表達在此類詩文中仍佔據主導性地位。就使臣自身而言,在此類詩文中,“使于四方,不辱君命”[46]的政治身份已經在日常化的文學敍述中淡出,賜予一品麒麟服、奉詔敕而行的政治身份也與其文化身份明顯疏離,使臣毫不隱晦地以文人或詩人自居,並將這種身份作為書寫詩文的直接原因。如龔用卿所雲“東國山川欲賞音,故教豪客放狂吟。清新未厭三千首,追琢能如百煉金”[47](《金巖館讀壁間諸作遂次其韻》);華察亦稱“綠樹黃鸝弄好音,慣於詩客助豪吟。酒闌慷慨飛霜劍,賦就鏗鏘擲地金”[48](《金巖館次韻》)等等。當使臣這種身份被自我確定後,文人所特有的文學生活化或生活文學化特徵則順理成章地在詩文中充分彰顯,如“我行離家將一月,得見好山多賦詩”[49](倪謙《抵浪子山》)、“留題笑我詩才拙,空負幽懷半日閑”[50](祁順《過臨津江舟中》)、“思詩馬蹶更吟詩,貪句渾忘蹶馬危……可是因詩今蹶馬,還憑詩句作神醫”[51](史道《途中馬蹶次韻》),從而為紀行詩文的日常化敍述提供了更為直接的身份支援。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域外記志詩為使臣的政治身份提供了向文學/文化層面拓展的空間,由於朝鮮特殊的政治文化語境的存在,致使這些域外詩作本身即帶有了政治敍述的色彩,特別是使事詩文與出使活動直接相關,在創作中使臣通過對帝國權威的吟詠以及朝鮮文臣的唱和共同營造出隆盛歡洽的接交氣氛,達成彼此之間的政治認同,進而鞏固了帝國的東亞秩序。但是與此相反,在紀行詩文中使臣仍以詩人自居,日常化的文學敍述仍在此類詩文中佔據主導性地位,使臣的文化身份並不因其政治身份的涉入而完全依附於政治敍述,而保持著自身的相對獨立性。正因為政治性敍述同日常性敍述產生張力,才為朝鮮官廳刊刻、以及朝鮮士人群體理解使臣的域外記志詩作,留下了可以多重闡釋的可能性。
二、域外記志詩在朝鮮的流布
在使臣離開朝鮮後,域外記志詩在朝鮮繼續流布,從中可以看到來自朝鮮官方和士人群體的兩種評判態度。
從官方來看,自天順元年(1457)陳鑒、高閏出使朝鮮後,朝鮮官方開始結集刊刻使臣的域外記志詩。這首先與當時朝鮮國的政治和文化氛圍有關。到十五世紀中葉,朝鮮王朝的政局漸趨穩定,政治制度的規範化工作也隨之起步,帶有國家大典性質的官方文獻都在此間編輯成書,如世宗二十八年(1446)《訓民正音》、世宗三十二年(1450)《東國兵鑒》、世祖四年(1458)《國朝寶鑒》、成宗六年(1475)《國朝五禮儀》、成宗十六年(1485)《東國通鑒》等等。正是在這種的氛圍中,直系“明帝國-朝鮮王朝”國家關係的出使活動及其文獻成果——域外記志詩,都被整理成為典籍以傳諸後世。域外記志詩的結集刊刻正是這種政治和文化氛圍的直接產物。此外更主要的是,使臣的域外記志詩的結集刊刻又與朝鮮的政治預期之直接相關,按照第一部《皇華集》(即《丁醜皇華集》,1457)序言中官方說法:
治世之音安以樂者雖然,以二公生質之美,學問之正,若不遇隆平之世,又何以鳴大雅之盛乎?至其因物寓懷,精確事理,揄揚振厲之旨,經緯錯綜之趣,則無非所以形容聖代泰和之隆也。噫!二公之詩,其形於言而極其和平者,雖自乎性情之正原,其所感之正,則莫非盛朝積累浸漬陶范化成之效也。
詩可以觀,詎不信夫吾東方邈在海外,世受皇恩,深仁厚澤,淪肌浹骨。今聖天子乃眷東顧,尤勤撫綏,所賜之敕至,曰:共用太平。此尤一國君臣,感激驚惶之無已也。我殿下拳拳裒集咳唾之餘,思欲印傳,永久與國人共之者,則悅二公文雅之美,而尤有感于聖天子寵綏之德之深,無所不用其極之意也。[52]
這段敍述中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帝國與朝鮮之間君臣的關係在序言中再次被明確,特別是朝鮮官廳將這種關係進一步表述為“尤一國君臣”尤其值得重視。按照《大明集禮》確定的禮儀構架的預設,雖然在國家廟堂之上的官員同朝鮮國王一樣是明帝國君主的臣子,但是他們的位置卻更為貼近帝國權力的中心。而作為朝鮮最高統治者的朝鮮國王(《大明集禮》中稱為“藩王”)僅僅是君主的“外臣”,它所統領的國家也僅僅是“外夷”,並不能進入同帝國的疆域同等看待。而這段敍述中,朝鮮官方在溥頌君德的時候,有意地拉近兩者之間的關係,將之描述為“尤一國之君臣”,其中雖不乏朝鮮試圖
- 上一篇:任增强:美国老庄美学研究路向
- 下一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
- ·世界汉学讲坛 | 何广思教授解读中拉
- ·阿根廷何广思:超越西方范本才能获
- ·阿尤布: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
- ·黄卓越:早期中国的书写与汉学研究
- ·薪火永相传,著名汉学家马克林讲汉
- ·《人民日报》:《用翻译架起中葡文
- ·蔡宗齐(美国):开辟中国文化走向
11 月 22 日下午,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北京语言大学主办、世界汉学中心承办的世界汉学讲坛第九讲成功举办。本次讲坛由...
10 月 18 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
日前,由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牵头建设的土耳其汉学家理事会在青岛正式成立,土耳其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土耳其著...
摘要:该文原为作者2021年10月20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举办的一带一路汉学研究论坛上所做的现场演讲,对海外汉...
2023年6月7日下午,薪火永相传大师说汉学暨世界汉学讲坛第四讲成功举办。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
2023年02月0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7版刊登了《用翻译架起中葡文化交流的桥梁》一文。文章由新汉学计划海外高级中...
天下学问一家: 开辟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新路径 蔡宗齐 蔡宗齐(Zong-qiCai),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校区东亚语言文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