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宝锋:美国汉学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缺失性”症候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23日第492期
【核心提示】海外汉学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呈现为一种“缺失性”症候,缺乏一种本土的话语承继性和自然性。这种“缺失”一方面使现代语境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保持了一种阐释的张力空间,另一方面也使本土与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之间保持了一种彼此敬畏的心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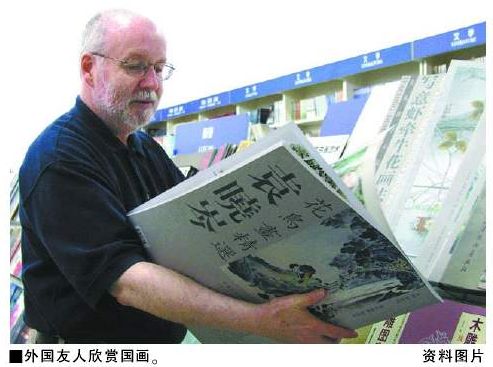
海外汉学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为国内学界敞开了一个较为宏阔的国际化视野,一些汉学家充分注意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影响,在研究中保持了一种较为客观和理性的眼光,并在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最大限度地克服了自身文化传统的局限性。但这些汉学家毕竟是一些“内行的外国人”,欠缺本土学者的文化意识结构。海外汉学家(包括那些在西方学术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华裔汉学家)在意识层面上有时可以完全是中国化的,但在潜意识层面,无法完全规避西方的学术训练以及文化传统对于其理论旨趣和观点走向的掣肘。随着文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西之间的对话日渐频繁,海外汉学和国内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差异性理解必将逐渐消除,不同理论形态的研究必然会共同助力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转型。
目前来说,海外汉学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呈现为一种“缺失性”症候,缺乏一种本土的话语承继性和自然性。这种“缺失”一方面使现代语境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保持了一种阐释的张力空间,另一方面也使本土与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之间保持了一种彼此敬畏的心态。
走出传统文论研究的“套板反应”
中国诗学只是海外汉学家所吸收的众多话语资源之一,很难说哪个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汉学家没有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过西方文艺理论谱系的影响。本土相对封闭的传统话语环境在汉学视域下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汉学家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时空范围和认知模式都有了较为新颖的界定。一方面,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引领我们走出了传统的文论研究的“套板反应”,使我们感知到中国古代文论进入古今和中西对话的强大能力;但另一方面,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毕竟以西方学者为主体,从话语领导权来说,汉学家们在研究中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正在逐渐构筑一个隶属于他们自己的话语体系,话语权因阐释者的影响正逐渐发生变异。在汉学的影响之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史的版图都将被改写,新的观念、看法、视角必然会给本土文论原有的观念带来冲击。从文艺学认知关系角度来说,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看似彼此独立,实际上存在一种彼此关联并相互影响的循环关系,三者当中的任何一种形态和认知理解的变化都会推动其他两种存在形态的改变。拿目前最具影响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来说,其对于六朝文学的倚重以及对于明早中期文学存在的强调自然会变革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情”、“采”、“文”甚或意识形态的认知取向。
理论问题的重新诠释和改写
一旦传统文学史的观念被挑战,那么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就可能在新的文学史形态背景下被重新诠释和改写,并催生出一种基于汉学理解基础之上的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全新话语形态。这种新的话语形态一经形成,自然会对国内学界的研究产生一种倾向性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海外汉学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西学语境和国际化视野,使部分表述体现出比较明显的与西方文艺理论谱系的交融与对话特征,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与西方现代文论的对接与互动方面显得相对自然而顺畅。然而,海外研究自身的中西理论隔阂还是难以避免的。因为虽然汉学研究的内容是关于中国的,但它是发生在域外、由“外国人”所做的学问;虽然材料、文献都是中国的,但是在学术规范和方法上乃至最终的问题意识上,许多海外汉学家难免从一个“他者”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文论。因此,要准确把握汉学生态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路向和特征,就必须认真理会汉学家的知识谱系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重构功能,就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任何以西方现成的理论直接套用在中国经验之上的努力都不免要沦为“削足适履”。虽然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意象主义乃至结构主义等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一些汉学家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解,但在面对海外汉学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时务必要避免一种无知而乐观的倾向,必须加强对汉学传统和理论语境的进一步了解,同时深入修正本土中国古代文论固步自封的研究状态,然后才能有效地推动其对世界的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发展产生积极的正态影响。
奇异的“他者话语”
汉学领域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尚未融入到国内研究的主流中来,其理论形态相对于本土研究的独立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这种独立性使汉学家们拥有了一种优于本土话语的前瞻性理解,同时阻止着汉学家们形成一种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透彻性理解。对于本土学者来说,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是一种与本土现成学术规范不同的奇异的“他者话语”,一种异质性的理论形态。这种异质性的理论形态的形成从客观上讲主要受制于海外的学术谱系、文化环境以及汉学言说的具体语境,从主观的层面来说,则和汉学家本身的知识谱系和趣味选择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学领域某一中国文论范畴的流行即是一种知识的选择,也是一种文化的选择,中国古代文论一旦脱离本土的话语环境和文化预设,其意义指向就必然会发生嬗变。另一方面,虽然先天就具备一种西学的视角和立场,但是汉学家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也是中国古代文论固有批评传统的阐释者,其任务和本土学者一样,是要延展激活并利用中国的理论,将之作为自身所处文化和文艺理论情境中具有“政治反应力”的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
要准确理解海外汉学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就必须融合汉学特殊的历史文化情境作整体之思;要从复杂的汉学生态情境中梳理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意涵演化轨迹,就必须基于一种文化视野和问题意识,多维度地介入中国古代文论的汉学生态结构,将研究纳入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中进行考察,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在考察其发生发展的基本特征时能够注意到汉学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进而准确梳理汉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形态及其在西方文论参照互渗过程中的演化逻辑,寻求中国古代文论在汉学意义系统中的当下合法性。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 上一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
- 下一篇:顾彬:《狼图腾》让我们想起希特勒时代
- ·索尼娅·布雷思勒与她“中国模式”
- ·翻译牵动文学命脉 ——访韩国著名翻
- ·链接中国:在澳洲研究汉学
- ·深研儒佛之道——梅约翰教授访谈
- ·翻译与研究:站在中国文学研究的前
- ·感受中国,书写中国 ——访加拿大著
- ·以语言与艺术为桥梁的汉学研究
人物简介 索尼娅布雷思勒(Sonia Bressler),法国作家,2005年毕业于巴黎第十二大学,获哲学与认识论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巴...
金泰成(김태성),韩国著名翻译家,韩国汉声文化硏究所所长。1959年出生于韩国首尔, 毕业于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 获文...
邓肯(Campbell Murray Duncan),新西兰汉学家和翻译家,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汉学系教授,现任《新西兰亚洲研究杂...
梅约翰(John Makeham) ,著名汉学家,现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拉伯筹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代中国哲学》(M...
伊维德(Wilt L.Idema),1944年出生于荷兰的达伦(Dalen),在荷兰莱顿大学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学。1968~1970年先后在日本札幌的...
李莎(Lisa Carducci)是加拿大著名的作家、诗人、翻译家和油画艺术家。早年曾就读于蒙特利尔大学,获文字学与语言学博士...
林西莉教授 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生于1932年。瑞典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也是作家和摄影家。自20世纪70年代起便致力于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