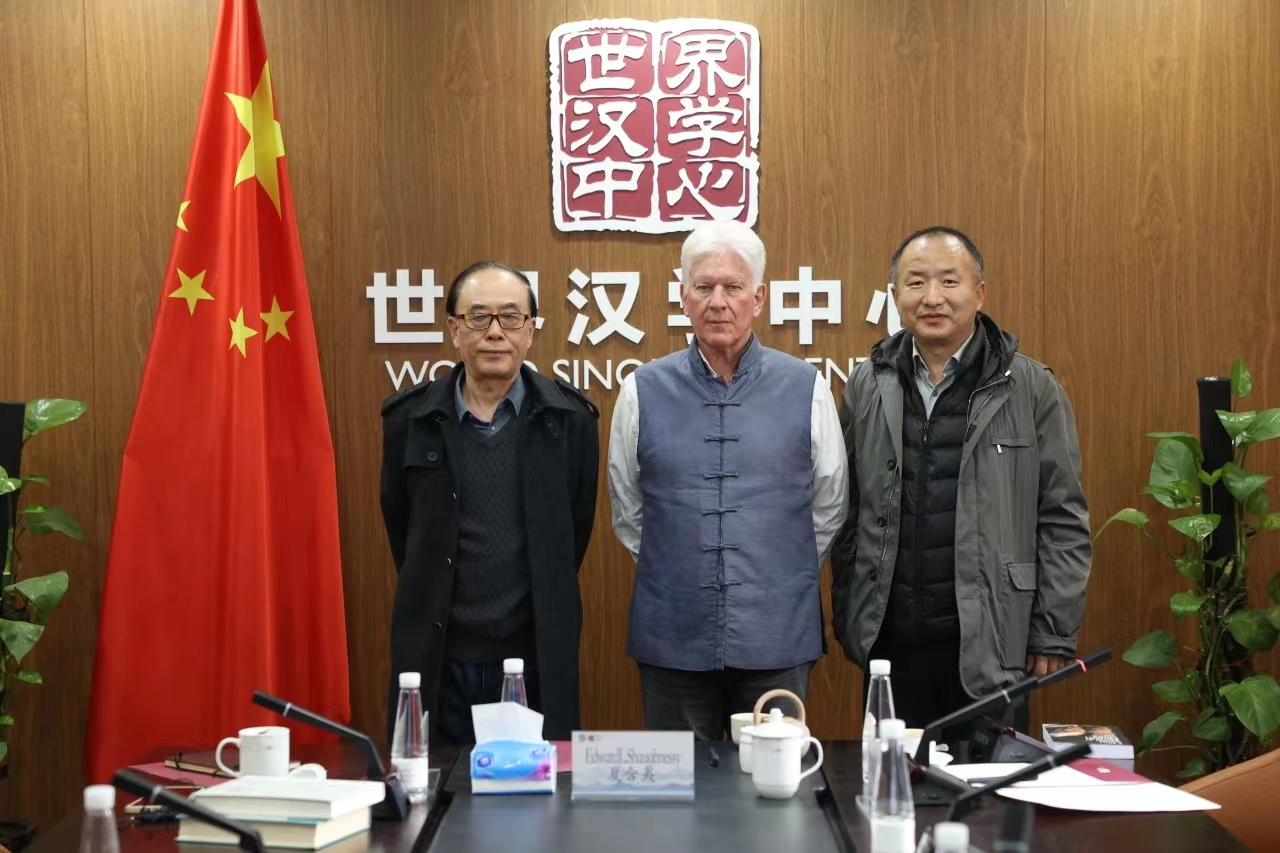张文瑜:文化研究视域下英国领事夫人笔下的新疆形象书写策略
张文瑜 :文化研究视域下英国领事夫人笔下的新疆形象书写策略
自英国在新疆南部重镇喀什噶尔(现在的喀什市)建立领事馆的1908-1948年间,有两位英国领事夫人来此居住,写下了游记,记录自己在新疆的旅居生活。首位英领事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Katherine Macartney)以她17年的喀什旅居生活为蓝本,著有《一位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An English Lady in Chinese Turkestan, 1931,后简写成《回忆》);最后一位领事夫人戴安娜·西普顿(Diana Shipton)撰写了《古老的土地》(The Antique Land,1950),记录两年随丈夫在新疆进行的探险活动。长期以来,对她们游记的研究主要是从史学角度,将其当作了解彼时喀什社会文化生活面貌的重要史料[1],忽略了游记书写中作者自身的文化影响以及彼时的社会历史语境,鲜有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进行考量。
考量到游记作者的英国领事夫人这一政治身份,及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本文主要采用文化研究的视角,从旅行书写与异域形象的关系着手,结合彼时的国际语境以及新疆的社会历史语境,以首位英国驻新疆总领事夫人凯瑟琳的旅居书写为分析文本,说明旅行书写中隐含的帝国书写策略——挪用、否定贬低、审美、自我确认,以及个人化,从而将新疆塑造成有停滞的、蒙昧软弱、却又充满异域风情的形象,一方面激发国内读者对新疆的占有欲望,另一方面强化英国(人)的先进性和优越性,美化和合法化英国侵掠新疆的种种行为。
一、 跨域旅行书写与异域形象的建构
旅行书写,作为一种旅行的呈现、再现和表达,深受读者青睐,因为旅行书写分享了跨域经历的印象与记忆,不仅满足了读者对未知的异域风情的欲望,更激发了读者对异域形象的想象。传统上,真实旅行的书写被当作旅行的忠实记录,成为史地学家研究历史与地理的重要素材。但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研究的兴起,现代跨域旅行成为一种跨文化实践,冲突的空间实践,涉及如何占有空间、如何在空间移动、如何使用、如何绘制地图以及如何表征。作为一种跨界行为,旅行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获得知识和自我身份的个人行为,而是“浸染着阶级、性别、种族和某种语言”的一项重要的文化、政治行为[1]。相应地,现代跨域旅行书写成为一种政治性介质——异域文化的阐释性文本和异域知识的建构文本,展现了旅行书写者对被旅行地的权力关系。
跨域旅行书写出现了表征危机,不再被认为是整个旅行的真实客观再现,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作者自身的身份与价值观影响的过滤生产,是一种话语。正如美国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E.W.Said)所说:“作者并不是机械地为意识形态、阶级或经济历史所驱使;但是我相信,作者的确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这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他们的历史和社会经验,也为他们的历史和经验所塑造。”[2]这些旅行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他们的旅行,但他们对表述什么?如何表述?作出了选择。这种重新的组织、整理和选择处理,以及讲述方式受到了语境、修辞、制度、政治和历史、作者身份等方面的多元决定,也注定会产生不同的异域知识和文化形象。
由此,旅行书写中的异域形象不是单纯地对现实的复制式描写,而是更多融入了书写者情感和价值的想象性建构,甚至是书写者社会的集体文化想象物的投射物。英国文化翻译家苏珊·巴斯耐(Susan Bassnett)声称:
旅行书写者是为了国内的消费者而创造他国文化形象的,因此,注定了将异国建构成他者。尽管旅行记录看似无辜,但总是携带着意识形态的维度,因为旅行者是从某一特定视角处理他/她的材料的......文本是为那些无法获得被描述文化的读者而写的。[3]
为了迎合国内读者的文化想象与期待,旅行书写者创造了一个他者的形象,但这种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在书写者、读者或国家意识形态的允许范围之内,是受到作者的先见影响的。也就是说,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文化中,对他者形象的塑造是不能任意而为的,旅行书写者既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建构者、始作俑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集体想象的制约。有些形象甚至是程序化了的,是一种编码,如西方对东方的他者形象的描写刻画,在萨义德看来,就是一种知识的建构,并通过体制与旅行书写将这种知识固定化并延续下来。
作为他者的异域形象,不仅是为了本国的读者所创造的,更是在“我”(陈述者或注视者)与“他者”(被陈述者与被注视者)的互动之中产生的,是为言说“我”而存在的。“‘我’要言说‘他者’,在言说他者的同时,‘我’又否定了‘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异国形象便表现为一种次要的语言,它与‘我’的叙事语言平行、并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替代后者以讲述出......其他话外之音”[4]。这种对立否定的“他者”形象却成为一种与旅行叙事平行的话语,传递出叙述语言之外的、注视者不愿表述或承认的文化事实。因此,对异域形象的研究重点其实是书写者、陈述者,而不是被陈述者。 相应地,对异域形象的探究,不是要探明“形象的真伪程度(就描述而言,所有的形象都是不真实的)”,而是致力于研究该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关系,研究一个或多个价值体系——描述的各种机制能够建立的基础”。[4]因此,在阅读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领事夫人的新疆游记时,不能单纯地将它们看作是对彼时新疆的真实呈现,或是通过史料比对这一形象的真实性,而是要追问“是谁在说?是谁在写?什么时候?在哪里?和谁在一起?写给谁看?说给谁听?在什么样的制度和历史限制下?”[5] 游记成为一种话语。正是基于如此的文化研究理论视角,本文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书写者,考察这些作品是如何被书写的,塑造了怎样的新疆形象?使用怎样的话语?书写的意识形态基础及其机制是什么?
二、领事夫人书写的社会语境
作为话语的异国形象既生产也反映其社会语境,因为任何异域形象的产生都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正如法国文学评论家达尼埃尔-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所言,“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4]自我与他者是一种主体间性,二者的关系也受制于当时两国的政治历史语境,讲述二者关系的形象具有不确定性.注视者在塑造异域形象时受到身份、先见、观看异域的时间、距离、频次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考据当时的国际形势、英国与中国新疆的关系、作者身份等政治文化要素成为考量外交官夫人笔下的新疆形象的关键。
新疆之于西方从不陌生,而是充满了吸引力。通过《马可波罗游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的英译本的记述,在欧洲人眼中,新疆更是充满了神秘、传奇、异域风情和古老文明。作为古代连接东西方丝绸之路的主场地,新疆自古具有了商贸、文化交流和军事要塞的重要地理位置。自1858年,印度完全被纳入英国殖民统治后,从地中海到印度之间的广大区域都成为英国的必争之地。十九世纪下半叶,恰逢清朝衰落与瓦解,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新疆成为一处开放地,成为英、俄等欧洲国家竞相争夺的角斗场。英、俄两国甚至在新疆南部重镇喀什(原名为喀什噶尔)建立了领事馆,扩大在新疆的势力,新疆不经意间成为两大帝国争夺的前沿。
正是在这种国际历史背景之下,第一位领事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于1898年与乔治·马嘎特尼结婚后,便从英国,穿过茫茫中亚来到喀什,并在此旅居长达十七年。作为外交官夫人,她必须站在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况她的丈夫是一位职业政治家,对英国的政治更是忠心耿耿②。英帝国于19世纪末达到顶峰:此时地球上85%的面积,已被贴上殖民地标签,帝国渗透于英国的各个生活层面不被帝国主义涉及。英国渴望打通埃及与印度的陆地联系,占有更多的土地中国新疆便成为英国的觊觎之地。更重要的是,凯瑟琳深知新疆对于英国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与自己丈夫的政治职责:
从政治上讲,中国新疆对我们大不列颠人来说,是令人感兴趣的。首先,它与我们的克什米尔的领土接壤,尽管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存在而交通状况及其艰难,在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却有一大批英属印度商人,他们驱赶着由马匹组成的驼队,从印度运来香料和曼彻斯特细棉布,又从这里向印度运去新疆的货物,如金子、玉石、和田地毯......中国新疆,或更准确地说,它的西南部分,就像阿富汗一样,处在中亚把印度和俄国隔开的地区;处在中亚把印度和俄国隔开的地区;由于俄国人一直向南扩张其边疆,维持这些起隔离作用的地区或起缓冲作用的国家的现状,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安排人盯着点是非常必要的。[6]
在彼时的新疆,英国的真正对手是俄国,需要拉拢的“朋友”是中国新疆,英国要以中国对抗俄国,从而保护自己的利益。作者丈夫的两个任务:“一是照管我们在那里的(英籍)商人的利益,二是监视俄国人在克什米尔边境方向的活动。”[6]这就决定了凯瑟琳对新疆的管理者汉族人与少数民族富人的“好感”,因为她认为只需将牧羊人拉拢过来就行,至于羊群,是不用估计他们的感受的。正是出于英国与新疆的复杂关系,凯瑟琳笔下的新疆形象也是复杂多面的,她对新疆的书写更是立足于当时的英国对新疆的战略之上,投射出英国的欲望。
三、凯瑟琳笔下的新疆形象与书写策略
凯瑟琳的身份和对新疆的先在认识,影响着对新疆形象的塑造。相对于十七年的生活,这本回忆录式的旅行文本是单薄的,只有184页,只挑选了些个别事件对自己的喀什旅居生活做了图式化的呈现。全书共十四章,其中三章都是在写英国与喀什之间的旅途艰难,但一家人都很勇敢、沉着、不畏艰难。其余十一章,通过选择日常生活中一些具有一定特征的人与事进行描述,强化了英国与中国新疆的差异性,塑造了新疆形象,并通过对比言说了自我。
(一)停滞的新疆与占用的书写策略
新疆的考古探险始于十九世纪末,一方面是随着非洲、美洲大陆探险的结束,神秘的中亚大陆成为探险者的诱惑之地;另一方面是沙漠中发现了古城遗址,吸引了欧洲学者的注意力。1890年在罗马召开的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决定组建一个“西域和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与民族国际考察委员会”。1902年在汉堡召开的新一届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这个西域国际考察委员会最终组建起来了。其总部设在西方列强中离西域最近的国都——俄京圣彼得堡。在国际委员会之下,还设立了各个成员国的国家委员会,由此,新疆,作为中亚的腹地,一处未被探考的,未被占有之地,吸引着一批批的欧洲探险者,掀起了各种探险热潮。多数新疆探险都是东方学委员会促成的。东方学是“通过作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7]从这种文本生产的机制看,对新疆的旅行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运作、西方权威的确定、对新疆的占有。
英国外交官夫人的身份使凯瑟琳认识大多数的探险者,甚至与有些人成为朋友,如奥利尔·斯坦因,冯·勒柯克。但她只是简略地概述而过,采用了典型的“占有”(appropriation)书写策略,为各国探险考古者对新疆文物的掠夺提供合理的借口。“占有”作为一种常用的帝国书写策略,是指西方认为地球上的一切理所当然是属于“文明”与“人类”,[8]而西方最能代表“文明”与“人类”,由是成为地球的合法继承者,剥夺了非西方的本地民对自己的土地和资源的利用。凯瑟琳首先将西方人在新疆的寻宝自然化。根据凯瑟琳《回忆》中的记述,当时的俄国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和她的丈夫是掀起考古热潮的始作俑者。其实在马嘎特尼没到喀什之前,“有一位英国旅行家——鲍尔上尉,曾意外地在新疆得到了一本手稿,极有文物价值。这件事引起了俄国驻喀什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的注意”,并开始搜集各种文书与古器具。而早在1893年,马嘎特尼“就得到了大量的破碎陶器、石质和金属印信、泥质佛教人像,35卷手稿——所有这些都是在巴扎上从当地的‘找宝人’那里买到的”。后来他将这些收藏品送到了霍恩勒(Hoernle)教授(加尔各答的一位著名的梵语学者)那里,并获悉这些手稿是“迄今所见到的最古老的印度文字手写文书”,“是公园4世纪的东西。”马嘎特尼与彼得罗夫斯基搜集到的文物文书,使“欧洲东方学者才开始意识到新疆这片大地为考古研究提供了一片新天地”[6]。是欧洲发现并挖掘了新疆的古老文明,本地人是无法胜任这一工作的。
将异域考古自然化后,凯瑟琳进一步将“占有”合法化。凯瑟琳对探险考古描述中,更是采用了谁发现就归谁的强盗逻辑。如,英国军官鲍尔发现的文书便以命名为“鲍尔文书”,并私自占有;斯坦因“首先发现”用纸书写的样本,“他有一件汉文文书,上面表明的时间与基督在世的时间相同”[6]。探险者从废墟遗址处带回了“数量极多的文书——几乎是用近20多种语言写成的”,这是他们的“辛劳得到了丰厚的回报”[6]。在探险考古的叙述中,新疆当地民是缺失的,国界也缺失了。作者更是大言不惭地让读者到大英博物馆,以领略新疆的古代文明,将占有合法化。
值得注意的是,凯瑟琳对考古的叙述是为了塑造出一个停滞的新疆,为占有新疆提供借口。各种文物的出土印证了“中国新疆过去曾存在高度发达的文明,也会认为这个地区曾是各种外来文化的交汇的。而这一切都出现在古代不列颠人用菘蓝中得到的染料绘画,在原始的橡树林中,表演各种各样令人可怖的用人献祭的仪式的时代。”[6]这种对比说明中国新疆的文明是属于古代的,现在已然失去了文明,停滞不前了;而英国却迅猛地从原始部落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的“日不落帝国”。新疆属于遥远的过去,属于古代,不是西方人当前的竞争者。中国新疆需要英国的帮助。所以“几个世纪都没有变化的古城”,在作者到来后慢慢变化,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停滞的新疆被纳入了英国的全球发展意识,成为驯化的对象。“占有策略中固有的包含在内与驯化”[8]成为《回忆》重要的书写特征。《回忆》中有四章都是在描写凯瑟琳的日常生活琐事,但从她那简·奥斯丁式的家庭生活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不仅乐意遵从英国的性别限制,成为“家庭天使”,而且将她在喀什的旅居生活环境英国化。她不仅从英国携带了各种生活用品,包括钢琴,而且总是从英国或印度邮购所需的物品;她按照英国的方式装扮了英领事馆,秦尼巴克(China City),改造了厨房,亲自下厨制作英国食品;甚至从英国带回树苗栽种在花园之中。这种对旅居空间的驯化对英帝国的巩固和扩张贡献颇大,因为她将有秩序的英国社会观念,携带着英国的文化价值与编码,输送了英国之外。当时的新疆也开始有更多的欧式建筑,甚至汉族官员都穿西装、系领带了。戴安娜来到秦尼巴克,更是将新疆与之作出对比,盛赞后者的舒适,前者的滞后,凸显出了停滞的新疆。凯瑟琳虽然受限于女性气质,但不妨碍她卷入帝国话语的生产,也不妨碍其强化英国的策略。
(二)蒙昧软弱的当地民与自我确认的书写策略
正如前面所言,对异域形象的描写是在意识形态允许的范围之内,当蒙昧肮脏成为东方形象的一部分固定下来,在描述新疆时,凯瑟琳也不可避免地强化了这一形象。在“喀什噶尔回城的街道狭窄,肮脏不堪......泥泞难行。街道两旁布满了阴暗的店铺,在有些街段,人们把苇席搭在街道上空,形成凉棚遮挡阳光,这样街道和店铺就显得更阴暗了......就在城门内,以及通向主要巴扎的街头,挤满了乞丐,他们中有很多人形容凄惨,让人看了很不舒服,原因是某些可怕的疾病或是使他们失去了四肢,或是使他们面容被毁,或是使他们变了形。”[6]在描述中,凯瑟琳使用了“肮脏”、“阴暗”、“凄惨”、“可怕”、“变形”这些常用来形容非西方地区和非西方人的词汇,构成了新疆的蒙昧落后形象。
凯瑟琳不仅描绘了城市的污秽,还不放过任何时机评论喀什噶尔人的不讲卫生。“孩子出生后几个月内不许为他们洗澡,小家伙浑身脏得一塌糊涂,在夏季烈日下,身上满是疮,有的得了皮肤病,有的得了眼疾”。[6]维吾尔族妇女只有在有重大活动时才梳头、整理,所以她们看似漂亮的辫子里都有虱子。即使是在汉族提台家里做客,各种精致美味的菜品也没能阻止凯瑟琳利用任何一个细节塑造新疆的肮脏形象。提台的一等宴会上,一个仆人,“捧着一条油腻腻的湿布,也在桌子周围伺候着,如果谁想擦擦手或脸,他就过来伺候。不用说,我一次也没使唤他。”[6]通过这种贬低化的描述,凯瑟琳始终以评判者的口吻强调新疆的落后,英国的文明。
为了进一步说明新疆的蒙昧,凯瑟琳刻意选取了几个事例,说明喀什噶尔人是蒙昧迷信的,没有丁点科学知识。孩子一旦有病,父母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只请巫医给孩子看病。得了天花的孩子外面疯跑,如果孩子死了,他们认为那是“安拉的旨意”。产妇为了顺产,临产前会找巫师,然后按照按照巫师的吩咐,照着一个木桩奔跑,即使是头晕眼花,昏倒在地,也要爬起来接着跑,直至巫师说她体内的邪魔已经驱逐出去了。由此可见,“喀什噶尔人不讲理性。”[6]众所周知,非理性是欧洲对非欧洲之外的民族进行描述时的关键词汇,可见,凯瑟琳自身携带着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
贬低他者常常也伴随着亵渎他者,凯瑟琳更是嘲笑了喀什噶尔女性在圣墓前哭泣以祷告的习俗。当地的喀什噶尔女性无法到清真寺去祈祷,所以,有什么想要实现的愿望,例如,想要有一位丈夫,就会到一些圣人墓去哭泣。凯瑟琳则带着嘲弄的语气说:“有时候我简直不怀疑,她们的祷告会很快地得到回应,因为我常常看见有些年轻人就在圣人墓周围晃来晃去,偷偷地窥视着这些祈祷者。”“极有可能的是,这些圣人们在活着的时候是些半疯的乞丐。喀什噶尔有许多这样的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有时甚至全家人都是这样,他们在古墓地一带晃来晃去,甚至就住在古墓中或圣人墓旁,当地人视这些人为特别神圣的人,从来不吝惜给他们施舍金钱和食物”。[6]凯瑟琳与来新疆的传教士们过往甚密,对他们传教失败的处境也很是同情与不解。如此一来,她嘲弄否定当地人的信仰习俗意图也就不难让人理解了。
贬低、亵渎或者否定他人的生活和习俗,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确定自己的优越性,即自我确认(affirmation)。所谓的自我确认是指欧洲白人认为他们有责任将欧洲的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通常是以“文明、人性、科学和进步为名的集体主体反复强调其价值,从而获得权力和主导地位。”[8]当地人的落后非理性,为欧洲人担负起“白人的责任”提供了机会。当时进疆的传教士便是一例,他们传播基督教失败,转而成立了医疗队。当地人得知凯瑟琳的孩子打了疫苗,就不再得天花后,开始领着孩子到领事馆要求打疫苗;当喀什噶尔产妇难产,当地人会破除自己是禁忌,请瑞典医生帮忙;欧洲人都乐意帮忙,并认为是自己的责任。正是在这种对比的描述中,出现了西方与东方,蒙昧与文明,科学与迷信,理性与宿命的对立。西方是进步的,是他们创造了历史,改变了世界。
自我确认的书写策略在描写“中国革命”一章最为明显。喀什噶尔人种混杂,不仅有对新疆进行管理的汉族和维吾尔族,还有柯尔克孜人、阿富汗人、印度人,还有具有欧洲人特征,不知是什么人种的俊男靓女。凯瑟琳笔下的辛亥革命是一场血腥的闹剧,闹剧之后,一切恢复原样。在混乱杀戮中,英国领事帮助了许多中国官员逃生,且在喀什噶尔的英国属民未遭受到任何财务与人员的,“英国的国旗”威严再次宣称了她的权威。当中俄发生了冲突,又是英国的总领事,马嘎特尼从中斡旋,避免了战火的发生。英国领事始终以“救世主”的形象在帮助软弱的汉族官员,保护当地的印度属民,这种自我确认的书写策略与作者丈夫在新疆到处发展印度属民的行径是相辅相成的。
(三)异域风情与审美化书写策略
为了能吸引读者,西方到东方的旅行书写往往会描述奇异的风景或风俗以强化异域的“他者”形象。这些描述都是从西方的观测视角,以西方的美学标准来凝视、描述和评判他者,即采用了一种审美化的书写策略。凯瑟琳也不例外。新疆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貌而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各种自然景观:沙漠、绿洲、山脉、冰川、湖泊在作者科学式的描述中,具有地理探险的吸引力,让读者对这里的生活充满好奇和想象,也容易使作者使用审美化的处理。
在这个地方,世界上的一些最高峰与地球表面上的对低洼点相互映照,共同存在于这里。以喀什噶尔作为终结点的新疆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峰(博格达峰)海拔24000英尺,帕米尔群峰中的塔格哈尔玛峰(Tagharma),高达25146英尺;在喀喇昆仑山脉中,高德温-奥斯汀(Godwin Austin)峰——人们更熟知的名字是K2峰,高度为28278英尺,据说是世界上第二高峰。然而与这些冰雪皑皑,高出海平面,直插云霄的崇山峻岭相对立的,却是低于海平面1000英尺,深深陷入吐鲁番绿洲的一个地方。[6]
这是怎样的一种视觉冲击,引发读者对新疆的无限向往。戴安娜也正是从阅读中获悉新疆的地理风貌,激发了对新疆的向往与痴迷。 凯瑟琳书中第四章的开头,写到:“就在我写这本书时,时时浮现出一种感觉,那就是我在书中把自己局限在家里及周围关系密切的人和事中,而且我也感到,这本书的读者——特别是其中无论如何也愿意了解范围更宽泛的事情的读者——会感到奇怪:难道我就没有什么材料和感受来谈谈整个新疆吗?......面对这样的读者,我打算在这一章提供一些不系统的材料。”[6]她本是应本书读者的要求,对中国新疆,按照自己的印象感受,简单描绘新疆的地理、历史等情况,但她却采用了如此科学的、冷静地书写方式,自信能从西方的观察视角描述新疆。凯瑟琳通过一种鸟瞰的,“上帝之眼”的方式对新疆的地貌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将相距上千公里的景观——乔戈里峰与吐鲁番盆地拼接在一起,使新疆的自然景观更加奇异化。
除了自然景观的异域化,各种文化风俗也展现了异域特色,引起读者无限的遐想。凯瑟琳本是要说明一夫多妻制给当地家庭带来的麻烦,但她却采用片段化这一审美书写方式描述了喀什噶尔妇女举办的节日招待会场景,从而将妇女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在招待会上,凯瑟琳坐在椅子上,其他妇女们坐着地毯上,身着做工精细、五彩斑斓的服装,浓妆艳抹,纤细的小手涂着红指甲,珠子和银链绕着脖子,甚至在长长的辫子末端也缀有珠子和银链。乐队音乐响起,所有的客人都站起翩翩起舞,她们舞姿优雅迷人。“在她们跳舞的过程中,双臂的摆动与回旋和音乐的节拍非常和谐......对这些跳舞的人来说,乐队的乐器只不过是一种美妙的声音来源,她们就是通过这种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的。”[6]喀什噶尔的妇女的美给人带来愉悦感,她们的这种生活也会让英国的“家庭天使”向往,忽略她们真正的生活现实。
在对新疆的各种文化风俗进行叙述时,凯瑟琳始终以权威的姿态、西方的美学标准来凝视、描述和评判新疆。当西方讲述东方的异域风情时,“性”是必谈的话题,也是西方将东方他者化的常用话题。西方人常常对东方伊斯兰国家的后宫和内室所体现的多配偶制、阴谋表示厌恶,但“西方的作家和艺术家再三地表现后宫这一主题,这一主题代表了一种在欧洲被禁止的不可触及的东方情节。”[9]作者在谈喀什噶尔的妇女时,谈到了当地的婚姻制度,一夫多妻制度。虽然一夫多妻与欧洲的文明是格格不入的,也是凯瑟琳反感的,但她却采用了戏剧化手法描写了一个事例:一位印度老商人在喀什噶尔娶了位年轻貌美的当地女子,当他要回叶城的家时,为了带走这位女子,颇费周折,最后还是收买了女子的朋友,骗过她的父亲才得以劫走。这种戏剧化的描述,作为审美书写的常用模式,赋予了书写者与观看者以特权,拉开了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距离,从而体现出她的欧洲中心主义。凯瑟琳厌恶一夫多妻,但并不同情这些喀什噶尔妇女的命运。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凯瑟琳笔下复杂的新疆形象是与复杂的国家关系、新疆与英国的复杂关系所确定的。正如“任何的文本表演都不是无辜的,我们总是将价值观铭写入我们的书写之中”[10],凯瑟琳笔下的新疆形象,不论是停滞的、蒙昧软弱还是异域风情,都投射了彼时英国对新疆的欲望与想象,是与英帝国的视野相契合的。作者采用的占有、否定贬低、审美、自我确认等书写策略是为了将英国占有新疆的意图和行径合法化。因此,书写异域从来不是无辜的,欧洲人的新疆游记有必要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洞悉其中的权力与意图,而不能将其看作是客观真实的表现。
注释:
① 对二十世纪欧洲游记的研究多是重溯新疆历史的文章。王恩春与裴杰生载于《新疆社科论坛》(2009年第2期)的《游记中的喀什噶尔——1864-1949的喀什社会状况》一文中以凯瑟琳的旅记为历史资料,梳理了1864-1949年间喀什的城镇、居民、宗教和教育,以及经济职业等方面的社会状况。闫存庭载于《新疆地方志》(2007年第3期)的《马达汉笔下的喀什噶尔述略》也将马达汉的游记作为史料,厘清当时的喀什噶尔各方面的社会状况。
② 中文名叫马继业,当时的印度政府驻喀什代表,1908年,英国在喀什设立领事馆后,任命他为总领事。他一心支持英国的帝国扩张。当一位夫人用喀什噶尔的跳蚤多阻止凯瑟琳到喀什时,马嘎特尼当即就回击说:“要是所有的不列颠人都只想那些跳蚤,我们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大英帝国?”见书中第111页。
参考文献:
[1]Clifford, James.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39.
[2]Said, E.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Vintage Books,1993:xxi.
[3]Bassnett,Susan&Lefevere, Andre. eds.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A].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33.
[4]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A].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02.
[5]Clifford, James &Marcus, George.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1986:13.
[6][英]凯瑟琳·马嘎特尼 著.王卫平译.戴安娜·西普顿著,崔延虎译.《外交官夫人的回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50.
[7]Said, E. W.Orientalism. Londonand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8:3.
[8]Spurr, David.The Rhetoric of Empire: Colonial Discourse in Journalism, Travel Writing, and Imperial Administration[M]. Durtham&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28.
[9][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85.
[10]Richardson,Laurel. Writing Strategies:Reaching Diverse Audiences.NewburyPark:Sage, 1990:12.
本文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2015年第二期
- ·世界汉学讲坛 | 何广思教授解读中拉
- ·阿根廷何广思:超越西方范本才能获
- ·阿尤布: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
- ·黄卓越:早期中国的书写与汉学研究
- ·薪火永相传,著名汉学家马克林讲汉
- ·《人民日报》:《用翻译架起中葡文
- ·蔡宗齐(美国):开辟中国文化走向
11 月 22 日下午,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北京语言大学主办、世界汉学中心承办的世界汉学讲坛第九讲成功举办。本次讲坛由...
10 月 18 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
日前,由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牵头建设的土耳其汉学家理事会在青岛正式成立,土耳其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土耳其著...
摘要:该文原为作者2021年10月20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举办的一带一路汉学研究论坛上所做的现场演讲,对海外汉...
2023年6月7日下午,薪火永相传大师说汉学暨世界汉学讲坛第四讲成功举办。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
2023年02月0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7版刊登了《用翻译架起中葡文化交流的桥梁》一文。文章由新汉学计划海外高级中...
天下学问一家: 开辟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新路径 蔡宗齐 蔡宗齐(Zong-qiCai),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校区东亚语言文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