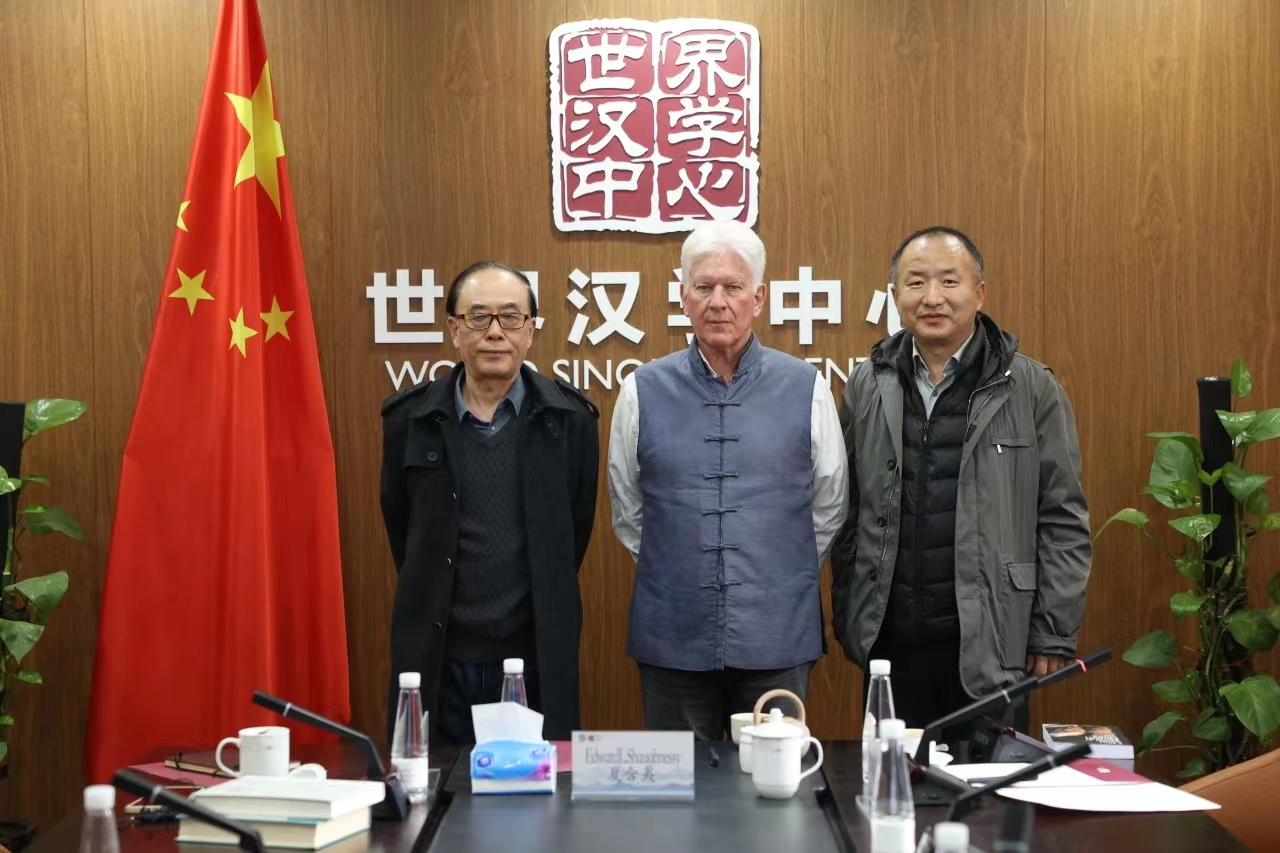黄卓越:从文学史至文论史
——英美国家中国文论研究形成路径考察
黄 卓 越
英语国家的中国文论研究经积年的累聚而至繁兴,目前已受到中国同行的频繁关注,其中,又尤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诸家的理论之作被介述最多。然考之于历史而知,英美地区的文论研究在最初实包含于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之中,而文学史研究又长期以来被裹挟在更大范畴的汉学研究中。这至少意味着文论研究作为一特殊的话域,与大汉学的框架,尤其是与邻近的文学史研究领域不仅关系甚密,存在一长时段并行的历史,而且文学史研究的发展也会对文论研究话语的构型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即以此为题,试图通过对一连续性进程的考察,探知文论研究是如何在一更大的学术语境中渐次构型,并最终演化为一相对独立的言说形态的。
(一)英国的端绪:20世纪前的研究
英语国家对中国文学的介述始于英国,这与英国在作为殖民帝国时间坐标上的位置有关。虽然一些中国典籍在17-18世纪已传入英伦,但几乎无人能够阅读,只有至19世纪初始,随着大批英国传教士、外交官员、商人与旅行者进入中国,不仅带回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信息与图书资料,同时也开始加强对汉语文学、中国知识与社会状况的关注,并出现了一个“前汉学”时代。[1]但此期对中国的介绍与研究基本上还是以自发、零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最初的那些研究者并没有固定的学科专业职称,几乎都是“业余汉学”(amateur sinology)专家,包括研究所用的图书与资料也多依赖于自己的收集,[2]早期的这种自发性研究往往属初阶性的,偏向于资料的编辑与情况的描绘,除了少量的撰述以外多显得比较表浅。但也有一些好处,即不受某一专业的规训与限制,可以将中国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与研究,[3]而这种特征也一直影响到了直至20世纪中叶的英国汉学的基本间架与研究向路。
随着汉学课程及汉学教授职位的设置,亚洲学/汉学研究机构的建立、专业性研究刊物的创办,英国汉学始被纳入到了一种组织化与建制化的程序之中。1837年伦敦大学学院设立了首个由牧师基德(Rev. Samuel Kidd)所担任的汉学教席,其后如伦敦国王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也相继设立了同名教席。当然,这并不等于在大学体制以外就不存在着汉学研究,而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依然并存着两种轨道即自发性研究与体制性研究平行发展的状态。19世纪初至20世纪早期的那些著名汉学家基本上仍是在学术的体制外成长起来的,在获得较高成就之后才受聘担任大学教授的职位,比如直到1920年,牛津大学在聘选第三任汉学教授时,还是相中了此前长期在中国底层从事传教活动、并有丰富著述的“业余学者”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再一,从早期汉学教席的名称上看,所谓的“Professor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虽然是依据基础教学的规划来设计的,但非一种狭义的学科称谓,除了当时的“文学”概念与后世狭义的文学概念有别以外(可见后文),另如19世纪至20世纪初年荣膺此教席的著名学者道格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理雅各(James Legge)、威妥玛(Thomas Wade)、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苏慧廉、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等,他们的主要成就虽或有些与汉语研究有关,但都主要不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而是均有广泛的学科兴趣与造诣(又以汉语研究、辞典及目录编纂、宗教学、政治学与文明史研究等为主),有一部分汉学家翻译了一些文学经籍或写过文学研究(狭义)方面的著作,但这些也仅是他们全部“汉学”研究成果中的很小一部分。
当然,如果总体上看,在英国早期的汉学框架中,也出现过许多涉及中国文学的文章,比如1832年创刊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58年创刊的《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72年创刊的《中国评论》(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等均有此类载文,其中又以作品的翻译与对文学史的简介为主,这也与此期汉学研究的大体水准是相当的。在约整个19世纪,以著作形式对中国文学进行集中论述的出版物主要有五种,即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的《汉文诗解》(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1830),苏谋事(James Summers)的《中国语言与文学讲稿》(Lecture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1853),道格斯的《中国语言与文学》(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 1875),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的《中国文学札记》(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1867),及1901年出版的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从各杂志的载文来看,麦都斯(W. H. Medhurst)在1875发表于《中国评论》上的《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一文在研究中国诗学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德庇时无疑是早期对中国文学倾力最多的一位学者,除几种泛义的中国研究著述以外,他翻译与编辑了数种通俗文学如小说与戏剧的作品,并在这些选本的引言部分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其中又尤对汉字与汉诗的构成特征有深入的探究。比如在《中国小说》(Chinese Novels)一书的引言中居然撇开小说问题,长段地论述汉字字符(character)的特点及声韵反切之学。[4]其《汉文诗解》刊发于1829年,是英国汉学史上首次评述中国诗学的专著。该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诗律(versification),也就是“在诗行、对句与段落中通行的特殊规则,以及这些要素是如何促成汉诗旋律与节奏的”;第二部分讨论“一般意义上的汉诗的风格与精神,其意象与情感的特征,并通过参比欧洲文学中采用的区分与命名法(nomenclature),对中国文学做出精确的分类。”[5]。为了理解汉诗诗律的特征,德庇时从汉诗的发声(sounds)、声调(tones, or accents)、诗节与音步(Poetical numbers or measure)、规律性停顿(pause)、尾韵(terminal rhymes)、句子的对应法(parallelism of couplets)六个方面展开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值的注意的是对“对应法”(parallelism)概念的解释,此概念原为Bishop Lowth在研究希伯来圣诗的诗律中总结出来的,并以为可以更细地分化为“同义对应”(parallels synonymous)、“对反对应”(parallels antithetic)、”综合对应“(parallels synthetic)三种类型。德庇时借此来解释汉诗及与欧诗的异同,以为没有一种语言能够像中文那样对之有透彻的贯彻,并以此形成一种特殊的美感。[6] 从总体面貌上看,《汉文诗解》是一部从汉语构成法的角度探讨中国诗学的理论性著作,在涉及中国诗艺的特征时,作者尽管没有引用传统的中国文论辞说,主要是根据自己对汉诗的研读体会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认知,但这些认知又没有停留在文学史/文学作品的层次上,而是触及到了那些潜藏在文本之中的组构性观念,因此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德庇时从汉语特征入手的诗解在后来对英美汉学中的文论研究具有持续性的影响,并形成了一种传统。就近而言,如麦都斯的那篇出色的论文在以英国诗人雪莱《为诗一辩》等提出的原则来阐明中西诗歌在表达诗与现实、情感关系上的一致性之后,即几乎是用德庇时的“对应法”切入对汉诗特征的解释,同时也做了更为丰富一些的论证。[7]
苏谋事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后担任伦敦国王学院第二任汉学教授,也是庄延龄的老师。他的《中国语言与文学讲稿》当是其在国王学院的课程讲义,大部篇幅放在对汉语构成规则的说明上,意在为汉语初学者提供一入门的向导。在这部分,苏谋事详细地分析了汉字的构成,即它的单音节词(monosyllabic)与象形文字(hieroglyphic)特征,以为由此而构成了与欧洲文字的重要区别,既然如此,“要想深入至一种语言的精神中,去发现它的美感,领悟到当地人在聆听此种语言时的感受,那么就有必要接受本土化的教育”。 [8]书末,撰者以“四部”为框架简单地介绍了中国“文学”的概貌,并十分简略地述及中国的通俗文学(light Literature)与苏东坡、李白等文学家。道格斯是继苏谋事之后出任国王学院汉学教席的第三任教授,他的《中国语言与文学》一书的副标题为“Two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可知与苏谋事的上书一样,出自课程讲义,并在结构安排上近似,第一讲介绍“中国的语言”,涉及汉字的特殊构造;第二讲讲述“中国的文学”,但这一部分的篇幅要远多于苏谋事的著述,并取之与欧洲的文学做了广泛的比较,显示出其一些独特的洞见。然其所谓的“文学”概念又与苏谋事近同,包含整个“四部”的范围(另再稍附加上戏剧与小说),尤其是提出儒家早期经籍(五经与四书),即“圣书”(sacred books),是中国“民族文学的一个主干”(the mainspring of the national literature),[9]因此而也从一特殊的角度表达了其对中国文学的看法。
伟烈亚力的《中国文学札记》是汉学史上以目录学形式出现的一部名著,全书分为四章,分别介绍了中国的古代经书、史籍、哲学著述与“纯文学”(Belles letters)的典籍,也正好合于四部的编排。书前有自己的一个总述,然后是抄录书目并作出简注。颇值注意的是该书中出现了一个“纯文学”的概念,当与泛义的文学概念有所区别,但其实中国传统目录学中的“集部”并不等同于纯文学,因此还是存在着概念上不对位之处[10],其绍介也只能扩展至所谓的纯文学之外。另一比较特殊的是伟烈亚力还为“诗文评”(Critiques on Poetry and Literature)单列出了一节,并在节前撰有一段简要的评释,以为早期的中国文学创作是自由与自然的,而后逐渐形成了某种“惯则”(conventional form),并进而发展为一种严密与有限定性的常规与诗法,成为一些著述所谈论的主题,并被称为是“诗文评”。虽然这些论述在目前看来更多地带有遗物的价值(antiquarian value),但可以借此去理解中国诗人的创作,因此也是重要的。[11]上述一段论述,也可看做是英语世界对中国文论最早的概念化表述。但接下的篇幅中伟烈亚力仅仅是从四库总目中摘录了一些书目而已,从其(因为受篇幅限制)首先著录《文心雕龙》,但却跳过钟嵘《诗品》、司空图《诗品》、欧阳修《六一诗话》等而直接续介陈师道的《后山诗话》看,他对这一领域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研究。
翟理斯长期以来担任涉华外事官员,其著述范围也很广,对中国文学的介述仅是其兴趣的一部分。[12]史称其著为首部文学史,这不仅在于本书的标题首次以“文学史”命名,也在于其呈示的章节容载了一个有序演进的文学史的完整框架(从远古至近代共八章)及含括了甚为丰富的内容,克服了前此介绍的零散性、随意性,使得知识的系统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次则,不再将文学史的绍介作为汉语教学的一个附证性说明,而是将文学史作为独立演化的系统予以论述,与之同时,不像苏谋事、道格斯等人那样主要以儒藏的编排方式来安置文学的归属,过度夸大儒学对文学的包容功能,而是充分地注意到老庄学派、佛教思想以及民间通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甚至以为其与前者形成了某种冲突性的关系,为此而将中国文学史构建为一个更为多元化的书写系统。当然,其关于文学的界义仍比较宽泛,[13]文学批评及其与文学史的互动也不在其视野之中,即便在其述及那些有丰富论文撰述的作者如王充、韩愈、苏轼等时,也不曾稍稍顾及他们的文学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在介绍唐代文学时,翟里斯却花费了较大的篇幅,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全部译成了英文,并以为其“在批评家的视野中占据着一个比较高的位置”[14]。尽管在翟里斯的意识中仍然是将司空图之作当做诗歌而不是诗论看待的,[15]然后来的中国学者一般都还是将这一举止视为是撰者对中国文论西传所做的一种贡献。
19世纪英国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情况大致如上,其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几个要点,首先,对中国文学知识了解的冲动只是早期汉学家整体汉学认知框架中的一小部分,被包含在大汉学的系统之中,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意识与取向,绍介的许多内容也多带有选择的偶然性,而且他们所谓的“literature”也还主要是一个泛文学的概念,从而也会影响到了对学科知识的界认。其次,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往往多从汉语文字与音韵的角度入手,这与早期汉学家的入门法径及实用取向有关,这也使对文论(中国文学观念)的一些察知会集中在这一维度上,而缺少其他方面的开拓。[16]进而,虽然中国文学自孔子以后即很难排除批评意识对书写的影响,文学史始终是与批评史的活动相伴随的,但是在英国早期汉学家的文学史介述中,却很少涉及到这一层面,他们中的若干人虽也曾通过文学史及其作品的阅读与分析,对中国的文学观念进行了一些发微与阐述,在某种意义上也带有“文论”的成分,但对更为理论化一些的批评学言述却甚少触及。就此而言,即便是从宽泛的角度看,此一阶段对中国文论的认知尚还属于处在十分懵懂的潜伏时期,初步萌生的那些幼芽也还是被包裹在了意义泛化的文学史襁褓中,难以脱胎而出。
20世纪以后,随着学院制的扩充与研究手段的精密化,英国的汉学有了递进性的发展并出现了一批鸿学硕儒,在文学研究方面,著名者有从事综合汉学而兼及文学研究的翟林奈(Lionel Giles)、阿瑟·韦利(Arthur Waley)、杜德桥(Glen Dudbridge)等,也有专治文学翻译与研究的霍克斯(David Hawkes)等。然而由前现代已奠定的研究模式对后期英国汉学仍具明显影响,综合研究始终占据着强势的地位,使得文学研究一直只能在此大格局的狭缝中生存,这种窘况既使文论研究难以受到关注,同时也因理论思维的匮乏加之方法的滞后等,使得对文学史的研究多流于表象的梳理与考订,缺乏更多的阐释层次。在整个20世纪中,英国方面可举出的文论研究实例很少,甚至如休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所撰的《文学创作法:陆机的<文赋>》(The Art of Letters: Lu Chi’s Wen Fu,1951),也还是其赴美国教学之后的产物,这也导致了有些颇富潜力的学者转教于美国(如白之、韩南等),并在后来也都被纳入于美国(而非英国)汉学家的名录之中。与20世纪中期后大放其晔的北美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相比,英国方面的研究实在是有些过于单薄了,由此而也需要将我们视线的转向北美(并在必要时连带英国)。
(二)北美的文论研究:一条渐次成型的轨迹
美国作为新兴的殖民帝国,与中国的接触比英国为晚,这也决定了其汉学起步会落在英国之后。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诚如一些学者已指出的,在19世纪,甚至直到二战之前,美国的汉学更多地是效傍英国发展起来的,这也会反映在汉学的基本构架、思路与方法等方面。加之许多重要的汉语文献已被英人迻译为英语,也为美国学人提供了甚大的便利。以此而言,至少在19世纪以内,美国汉学在文学史译介等方面没有太多可述者。以中国文学为专题的著述目前可见的仅有传教士罗密士(Rev. A .W. Loomis)所撰的《孔子与中国经典:中国文学读本》(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 O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ture,1882),此书前两章介绍儒家的史书及“四书”,第三章介绍了十几种儒家书写的文体(含短文、碑志、谚语、格言等),从今天的角度看,大致可归为一种专题性介绍。[17]此外值得一提的便是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在《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dom,1848)中所设的“中国的雅文学”一节,以“四部”为名逐节分述,并列举了欧洲尤其是德庇时对汉文诗歌、小说与戏剧的英译情况。丁韪良(William Martin)兼涉文学的汉学著述有《中国人:他们的教育、哲学与文学》(The Chinese: Their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Litters,1881)[18]、《中国知识,或中国的知识阶层》(The Lore of Cathay,or The Intellect of China,1901)[19], 二书有一些共同之处,即均将笔墨集中在对传统中国一般知识体系的介述上,并将文学作为整个体系的一个部分,这与丁韪良长期以来担任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席的职务有密切的关系,由此又称这些文字为“Hanlin Papers”(翰林文集)。丁氏二书的文学介述部分有许多重复的之处,并多聚焦于对各种书写文体(如诗歌、散文、书信、寓言等)的分类描述上,其目的是使西人对中国文学书写有一初步的了解。比较特殊的是丁韪良的叙述有三处简约地提到了孔子的诗学观,[20]也可看做是美国汉学对中国文论的最初援引。从中也可见,无论是卫三畏还是丁韪良,对中国文学的介述都是被安置在整个大汉学谱系之中的,并没有显示出对文学的独立关怀,因此也不可能进行深入与专业化的研究,这与早期英国汉学的知识取向是基本一致的。
文学史与文论史(广义的)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涉关系,但从发生的意义上看,后者对前者的依附是更为显著的,这是因为文学批评与理论的思维客体便是文学活动,无文学的活动,也无所谓有关文学的批评与理论。与之同时,文学作品是普遍可赏的,而文学批评与理论则属于更为智识化的活动及对深层文学规则的解释,从而也有赖于更为专业化的投注。也正因此,几乎所有民族对异国文学的了解均是从文学史(作品)入手的,走在对批评与理论的研究之先。在汉学发展的早期,英美对中国文学一般知识的获取尚处初步的阶段,自然也很难对之做更进一步的要求。就此而言,对文论史的关注,首先还有待于文学史研究的展开、成熟与深化,而这进而又有待于文学史研究能够从大汉学的框架中分化出来,借此以获更为明晰的学科界认,并趋之而入能够精耕细作的专业化轨道。当然,从北美的情况来看,中国文学史研究在20世纪的繁兴,既与一般的规律或趋势有关,比如汉学(东方学)作为一种研究类型受到国家机制的重视与扶持,文学学科的建立及文学研究成为民族教育体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等;同时又有一些特殊的助因,比如本地文学创作对中国文学资源的吁求,可观数量的华裔学者的介入等。正是这些条件综合在一起,促成了中国文学研究在北美的勃兴。
需要在此对美国创作界对中国文学资源的吁求做点解释。这种吁求主要集中在对汉语诗歌的引介与摹创上,史称共出现过以“东方精神的入侵”为话题的两次浪潮,即1910年代发端的以庞德(Ezra Pound)、洛威尔(Amy Lowell)等为代表的“意象主义”(Imagism)运动,与1950年代中始的以W. C. 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雷克斯洛思(Kenneth Rexroth)、斯奈德等为代表的“旧金山文艺复兴”(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运动。
两次汉诗推进运动通过译诗、论诗与仿诗等行动,在美国诗坛造成了甚大的影响,已有学者对之作出详尽的论讨,似毋庸喋述,[21]然而扩展地看,其也对美国汉学界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需要作出重估。首先是两次运动翻译出了大批的汉诗(也包括学院派的译诗),展示了中国文学的奇迹般创造,丰富了中国文学史的知识谱系,这当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催发与提升北美场域的文学史研究意识。从随后的研究看,美国汉学界的文学研究多集中在诗学领域,也可看做是与受到两次汉诗运动的感染与启发有关,甚至表现为对汉诗运动的一种侧面接应(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汉诗运动推崇的那些诗人如陆机、陶潜、王维、李白、白居易、元稹、寒山、苏轼、杜甫等也恰是后来美国汉学界选择研究的重点人物。其次,汉诗运动将对中国诗歌的理解集中在具有突出审美特征的文字意象(前一波)、禅道诗境(后一波)上,也对汉学界文学观念的转换有一定的影响,即相比过去对文学谱系的宽泛把握而更收缩了文学的界义范围(也与美国20世纪初以后的文学观念转换恰好合辙),使“纯文学”的概念能够逐步从泛义文学的概念中游离出来,直至确立牢固的地位。另外,无论是意象派诗人还是禅道派诗人,都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读”出了汉诗中所蕴含的诗学内涵,并用偏于感性的方式对之做出了提炼与总结,比如庞德的“表意文字法”(ideogramic method)等,这些虽然还属于“文学观念”的范畴,但对汉诗诗学理论的建构也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并会启发汉学界沿此而对中国文论做进一步的探入。关于后一点,最为明显的例证是在第一波浪潮之间,张彭春(Peng Chung Chang)受美国著名批评家斯宾加恩(J. E. Spingarn)的约请翻译出了严羽的《沧浪诗话》,这也是因为严羽这部著作的思想取向被看做与汉诗运动的理念是相吻合的,[22]尽管此时的文论涉入还是属于附带性的。汉学研究界受汉诗运动直接影响可举的例子非常之多,如著名的陶诗与文论研究者海陶纬(James Robert Hightower,)便是因年轻时受庞德英译汉诗的感染才决定选习汉学的,哈佛大学汉学教授华兹生(Burton Watson)在60年代译出了在第二波运动中被推为桂冠诗人的寒山的百首诗歌,[23]1951年译出陆机《文赋》、60年代撰写《<诗品>作者考》的方志彤(Achilles Fang)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庞德,叶维廉(Yip Wai-Lim)不仅是第二波运动的亲身参与者,也专门撰写了《艾兹拉·庞德的<神州集>》(Ezra Pound’s Cathay)一书,[24]这也带动了他对与运动趣旨相一致的中国文论研究。更大而言之,70年代后汉学家热衷的汉字“意象”研究、汉字声律说研究等,同样是在承应庞德等意象主义叙述(并引入了新批评等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二战之后,美国的汉学/中国学研究开始升温,不仅摆脱了欧洲传统汉学的影响,而且在经一段时期的积累之后取代欧洲而成为国际汉学的中心,中国文学研究作为一专业方向也初步得以确立。刘若愚(James L. Y. Liu)1975年发表的《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当前的发展,流行的趋势与未来的展望》(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st: Recent Developments, Current Trends, Future Prospects)一文对60年代以来出现的景观做了描绘,其中包括专家学者、出版物与会议等的大量增加,英语成为主要的工作介体等。其次,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中国文学研究已逐步构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再隶属于传统汉学。[25]关于后面一点,经我们的考察,在1975年之前北美地区的文学研究名家除少数几位,他如华兹生、海陶玮、陈世骧(Chen Shih-Hsiang)、白之(Cyril Birch)、夏志清(Hsia chih-ching)等,及声名初显的韩南(Patrick Hanan)、刘若愚、叶维廉等均将文学作为毕生研究的专业目标,此种趋势于75年之后就更为突显了,学科细化的进程已成为一种研究的常态,使学科发展的驱力大大加强。为此,在60年代,也出现了数种较大跨度的专门研究(如华兹生的三种著作),及用英文撰写的文学通史类著述与研究辑本。从60年代出版的三种文学通史[26]的面貌即可看出,尽管叙述上还比较表浅,但其梳理均已明确地集中在狭义“文学”的概念上,与早期英人的文学史撰述理念已有较大区别。
也正是在学科独立与文学史研究升温的趋势带动下,北美的文学批评也始被纳入到了研究的日程,当然也可将此视作是文学史研究深化的一种副产品,这也因早期进入该领域的学者基本上都是从文学史研究起步而兼治批评史的。据涂经诒(Tu Jing-I)的回顾,他认为大约从1950年代始,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受到学界的重视,出现了一些重要译著与论著,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27]就翻译来看,像典型的文论著作陆机《文赋》、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司空图《诗品》等均在此期被译成英文,并有了相当一批对之的专门性评述与研讨。[28]在60年以前,像陈世骧、海陶玮、方志彤等的文论研究也已达相当的深度。60年代之后(至1975年),除了原来的研究者继续在这一线上耕耘,新的研究者也始涌入这一伍列,此期专著还甚少见,但论文发表数量却已大为增多,涉及到批评原典、批评家、批评观念与概念等方方面面。另一新的现象是出现了以中国文论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包括英国方面也有介入。这些学位论文中比较重要的有麦大维(D. L. McMullen)的《元结与早期古文运动》(Yuan Chieh and the Early Kuwen Movement,1968)、黄兆杰(Wong Sui-kit)的《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情”》(Ch’ing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1969)、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的《作为批评家与诗人的王士祯》(Wang Shih-chen as Critic and Poet,1971),后来此三人都成了英语世界文论研究的中坚。
在此之际,另外一种情况需要注意,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1995年《唐研究》(Tang Studies)上发表的纪念傅汉思(Hans Franlel)一文,认为60年代是美国中国文学研究产生根本性嬗变的时期,而傅汉思在其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他使他的学生们认识到,这个领域除了重要的汉学家之外,也是由欧洲和美国的主要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所构成的。”[29]在这一叙述中,我们见到了一个触目的字眼:“理论”。其实早先的批评史研究本身也是面对理论的,那么宇文所说的这一理论必然会有所指,即用西方理论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文学、文论等。如实地追溯这一进程,60年代中期后发生的一些理论转向还主要是用某些西方文论来诠解具体的文学史与批评史文本,比如傅汉思1964年撰写的《曹植诗15首:一个新的尝试》(Fifteen Poems by Ts′ao Chin: An Attempt at a New Approach),即已尝试摆脱以“生平和人品”论诗的旧套,将新批评的方法用于解释文本。[30]在其1976年出版的《梅花与宫女》(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中,此种用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推进。用各种西方理论话语来分析文本的做法,至70年代始蔓延于文学研究界,高友工(Kao Yu-kung)与梅祖麟(Mei Tsu-Lin)在1971年合撰的《唐诗的句法、用字与意象》(Syntax, Diction, and Imagery in T'ang Poetry)一文,已能稔熟地用结构主义语义学及新批评等的方法来分析唐诗,进而从形式的层面上厘定出了中英诗歌之间的差异,[31]产生出一种令人着迷效果,并昭示了一种新的研究径路。再后于诗学研究中有宇文所安、余宝琳等,在小说研究中有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浦安迪(Andrew H. Plaks)等都曾使用新批评、结构主义与叙事学等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由此形成一壮观的波流。
在一个总体性的面向于理论(或文论)的趋势中,可以分为几种方式,一是已述的将中国文学批评与理论的著述、人物、术语、思潮等作为对象的研究(包括译介),可简称为“理论的研究”,主要为50年代之后出现的一种文论研究方式,并以“以史为证”作为其主要的方法(这是我的概括)。第二种是约在6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援用西方文论具体诠解文学史与批评史的研究方式,可简称为“理论的诠释”。第三种是在进行大规模的综合之后,从一种理论及一套概念的框架入手来建构中国文论的体系,此种方式主要兴盛于70年代中期,可以称之为“理论的建构”。当然在实际的运作中,有时二、三两种方式间也存在着界限不明之处。70年代中期以后,北美文论的发展呈现为三种路径并行发展之势,但就时序上来看,上述的这一前后交替进程也显示了文论研究日趋“理论化”的轨迹。我们注意到涂经诒在归纳这些模式时,还加上了一项“文类研究”(genre Theory),[32]这也是60年代之后被汉学界经常述及的。文类学固然也属于中国文论的一部分,如从曹丕至挚虞、刘勰、萧统,再至明代的吴讷、徐师曾、许学夷等形成了一特殊的描述系统,但针对原典的分析常可纳入到第一种模式即“理论的研究”中,有些文类研究只是在面对文学作品时有一个初步的划分雏形,则可归入文学史的研究中,除非是专对文类进行理论上的辨析或构造,才可归至后两种研究模式之内(比如倪豪士的研究),因此,将之看做文论研究中一种特例可能更为合适。
第三种研究方式即“理论的建构”,可以刘若愚《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的出版作为一转折性的标志,因此也可将1975年看做是第三种范式的确立之年。为将自己的研究构造成一种名副其实的“理论”,刘若愚首先从已有的西方文论中选择了两套论述的框架,作为搭建整体性言说的基础,这也就是韦勒克的三分说与艾伯拉姆斯的四分说。韦勒克的三分说即认为可将所有的文学研究分为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三种类型,将文学批评看做是指“实际批评”,而将文学理论看做是对更为抽象的一般性原理与规则的研究。[33]尽管刘若愚认为文学理论也有赖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成果,但却属于更高层面上的研究。有鉴于过去的批评史研究多满足于事实的叙述,而乏系统的阐释,因此而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工作构建出一套具有整体囊括性,同时也对“世界性的文学理论”有所贡献的中国文论体系。[34]艾伯拉姆斯的四分法属于在已经分疏出来的“文学理论”的大概念之下建立的既能对文学的基本要素加以区分,同时又能给予各要素相互联系之解说的一套学说,这些基本要素包括宇宙、作家、作品、读者,并相应地对称于四种理论即模仿理论、实用理论、表现理论与客观理论。考虑到中西文论之间的异同,刘若愚在经过调整之后将之改造为六种理论,即形上论、决定论、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与实用论。[35]全书以下的论述也就围绕着此六论展开(并以更为丰富的西方文论作为附证),从而最终“结构”出一个逻辑完备、转承优雅的有关中国文论的巨型体系。而根据刘若愚采用的韦勒克的三分法,那么文论研究也就不再被视为文学史研究之下的一个隶属话题,而是与文学史研究具有平行位置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个命题非常重要,即反映了其欲将文论研究从一种混沌不分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史研究的大格局中区划出来的明确意识。尽管在美国的文学研究场域中,这种学科划分的提法很难获得体制上的支持,但仍颇具观念上的革创性。
刘若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诗学领域,其所采用的方法,是将宜用的史料从原来的生成语境中抽取出来,分别纳入其所预设的理论网构中,以一套经过精心构制的概念来带动与统合整个叙述。尽管这一工程很难被二次仿效,但是作为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范式性冲动,必然也会伴随有更多的实践及会带来扩延的趋势。比如在叙事文学领域,便有浦安迪在70年代中期以后所做的尝试,其所构造出的那套“叙事理论”模式,通过持续地援用多种西方批评理论(原型理论、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与小说修辞学等),来探察中国叙事文构成特点,从而在早期小说研究者如韩南、白之、毕晓普(John L. Bishop)、夏志清等所惯用的实证主义模式之外,转换出了一条研究的新路。[36]在比较诗学领域,则有叶维廉的“模子“(modle)说,以原型论为基础并设置出各种概念分层,旨在借助一套新的解释原则为中西诗学之融通提供一揽子解决的方案。[37]高友工在完成唐诗的概念化研究之后,甚至有所放弃“文学理论”的概念,而用更为抽象化、哲学化的“美学”概念来命名与打理自己的学说,遂将陈世骧早期基于文字与具体文本考察而提出的“抒情传统”(Lyrical tradition)演绎为一种带有普遍规则性、文化全涵性、历史贯通性与精神超越性的 “抒情美学”( Lyric Aesthetics)大体系,或其自云的是一种带有更大整合性的“统一理论”(Unified theory)[38],也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39]。此间其他用“美学”概念来运演中国文论的事例也甚多见,如更为年轻一代中的苏源熙(Haun Saussy)、蔡宗齐(Cai Zong-qi)等即是。
在此种风气的导向下我们看到,“理论”的概念在1975年之后开始频繁地被用之于文论的叙述,许多文章的标题都措用了“理论”的字眼。这种影响也见之于一些选集的编订,比如宇文所安199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Reading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虽然批评了刘若愚等以“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为标目从文本中抽取概念以自创体系的做法,[40]但其文集的选目也依然集中在几种理论化程度偏高的古典文本上,明显地是以“理论”而非“批评”来鉴别文本的价值。与之同时,过去在原发性批评史上罕有论及的专著《文心雕龙》不仅成为汉学研究的第一大热门,探者如云(与中国此期的情况也相一致),而且其地位也被提升到压倒其他一切批评性言述的高度。比如高友工在其《中国抒情美学》的长文中以为中国文学批评的进步是与对理论兴趣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并终至《文心雕龙》的出现完成了对“总体文学理论”(total theory of Literature)的建构:“确切而论,《文心雕龙》既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第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具有讽刺地,也是最后一部作品。”[41]而该作的力量,源于其试图从总体上(totality)处理文学现象的勃勃雄心。早期与高友工合作撰文的梅祖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提到他们在70年代进入文论研究时,最为崇尚的两部中西著作便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与弗莱的《批评的解剖》,并均可以“体大思精”称之。[42]进而,《文心雕龙》也被作为一种最高的标准用以反思中国文论批评形态之不足的依据,其中加拿大学者叶嘉莹的论述就很有代表性,如其在70年代完成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即以为“除了一部《文心雕龙》略具规模纲领之外,自刘氏以后一千多年以来,竟没有一部更像样的具有理论体系专门著作出现”,其他都属“体例驳杂”之作。[43]探其原因,即最终可归于中国传统中缺乏西方固有的理论思辨能力与习惯。即便如刘氏之作,其能成为一种体系化的煌煌巨著,也还是因于作者受到了外来佛典思维的影响,而其不足,比如批评术语的“意念模糊”等,则与作者的本土性习惯思维有关,由此推论,王国维的诗论同样呈现出优劣二分的特征。[44]而最终的结论,则是期盼中国学者能积极借用西方理论的精密工具,打造出本土的文论经典。
(三)余论
借助以上的追溯,大致可对中国文论研究在英美的展开历程有一概览,这个历程由两大进阶构成,从外部来看,表现为从大汉学至文学史研究,再至文论史研究的进阶;从文论研究内部看,则又表现为从“理论的研究”至“理论的诠释”,再至“理论的建构”的进阶,两大进阶又共同刻绘出了一条文论独立与“理论”自身不断攀升的运行弧线,从而展示出了在英美的汉学语境中中国文论言说谱系逐渐构型的历史。当然,这种单线式的描述还仅是就一种趋势而言的,并不代表实际场景中所发生的全貌,也并不等于在某一阶段,比如说在第三阶段上就不存在着前两种模式的研究,而是各种模式仍然均有自己的进路,并一同构成了70年代后的文论繁荣。与之同时,从文学史中彻底分化出来的提法也只是一种理念的倡导而已,实际的情况却是更为含混与多样的,此外,既然在英美的学术建制从未出现过“文学理论”这样一种学科安排(像中国那样),那么文论研究与文学史研究兼治的情况也是普遍地存在于多数学者身上的,与之同时,文论研究也始终只是作为一种独特的“话域”,而非独立的“学科”处身于文学研究的范畴之中。
英美文论研究界的理论阐释与理论建构活动在大约经历二十多年之后,至90年代中期后已趋降衰,这与这些模式在学理上的局限及整个北美的学术风气转向皆有关系,后者主要表现为以“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为代表的各种新探索在近年的涌现。这也已为许多汉学家所述及,遗憾的是国内对之的反应还略显迟钝,因此在介述时难免出现夸大70-90年代研究的现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只是目前的研究所依据的是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及被语境的论证有力限定的探索。鉴于篇幅,关于这一新趋势对文论研究带来的影响,只能允我在另文梳理。
原刊于《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4期
※ 此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海外汉学与中国文论”(08JJD751070)的阶段性成果。
[1] 德庇时在19世纪初曾曰“中国文学在英国的发展几乎完全是本世纪的事,……直到上(18)世纪末,还找不到一个懂汉语的英国人”参John Francis Davis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and”, Chinese Miscellani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 London, John Murray, 1865, p50.
[2] 关于这一叙述可参鲁惟一(Michael Loewe), “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K”,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No.7,1998.
[3] 参鲁惟一,“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K”.
[4] 参John Francis Davis, Chinese Novels,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 London, John Murray, 1822. 该书本为中国小说等的一个选集,然在书前有一50 页的长序“Observations on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除介绍中国小说的特征之外,后半部分转向论述汉语语法的问题,其中也多涉及马礼逊有关汉语音韵学的论述,并提到沈约的“四声说”。
[5] John Francis Davis,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London, Asher and Co., 1870, p1.原文发表于1829年。
[6] John Francis Davis,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pp25-28.
[7] W. H. Medhurst, “Chinese Poetry”, The China Review, Vol.4 no.1, 1875(Jul).
[8] James Summers, Lecture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London, John W. Parker and Son,1853,p11.
[9] Robert Kennaway Douglas,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 London, Trübner & Company,1875,p76.
[10] 伟烈亚力事实上也注意到此问题,因此在介绍这一部分时也解释到: “…Chinese Literature Termed 集 Tscih, may be not inaptly designated Belles-lettres, including the various classes of polite literature, poetry and analytical works.” A.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first edited in 1867; Reprinted in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12, p225.
[11] A.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pp243-244.
[12] 在选编与翻译文学之外,翟里斯其他方面的著述还有20多种,借此可见其绝非以文学研究为专长。
[13] 翟里斯对“文学”的概念有些分疏,比如以“miscellaneous literature”,“ classical and general literature”两个概念来概括不同的品类,但是像《四书》、《五经》等仍在其列目中,又如一些更为泛化的著述如法医学著作、《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均有专节介绍,可见其文学概念仍比较混杂,这与当时英人对文学概念的理解直接相关。Herbert Allen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andLondon,1901.
[14] Herbert Allen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p179.
[15] 此后出现的如L. Cranmer-Ryng(1909), J. L. French(1932), C.M. Candlin(1933)等的译文也都是将之作为诗而非诗论收入的。
[16] 这种实用主义倾向均可从上述德庇时、苏谋事与道格斯著作的引言中见到,反映出了近代殖民主义的核心理念。而此种倾向的长期延续,也为英国的许多的汉学家如阿瑟·韦利等论及并有诟病,最尖锐的批评可参Timothy Hugh Barrett,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London, Wellsweep, 1988.
[17] Rev. A .W. Loomis, 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 O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ture, San Francisco, A. Roman, Agent, Publisher ; Boston, Lee and Shepard, 1882.
[18] William Martin, The Chinese: Their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Litter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81.
[19] Wil
- ·世界汉学讲坛 | 何广思教授解读中拉
- ·阿根廷何广思:超越西方范本才能获
- ·阿尤布: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
- ·黄卓越:早期中国的书写与汉学研究
- ·薪火永相传,著名汉学家马克林讲汉
- ·《人民日报》:《用翻译架起中葡文
- ·蔡宗齐(美国):开辟中国文化走向
11 月 22 日下午,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北京语言大学主办、世界汉学中心承办的世界汉学讲坛第九讲成功举办。本次讲坛由...
10 月 18 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
日前,由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牵头建设的土耳其汉学家理事会在青岛正式成立,土耳其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土耳其著...
摘要:该文原为作者2021年10月20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举办的一带一路汉学研究论坛上所做的现场演讲,对海外汉...
2023年6月7日下午,薪火永相传大师说汉学暨世界汉学讲坛第四讲成功举办。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
2023年02月0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7版刊登了《用翻译架起中葡文化交流的桥梁》一文。文章由新汉学计划海外高级中...
天下学问一家: 开辟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新路径 蔡宗齐 蔡宗齐(Zong-qiCai),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校区东亚语言文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