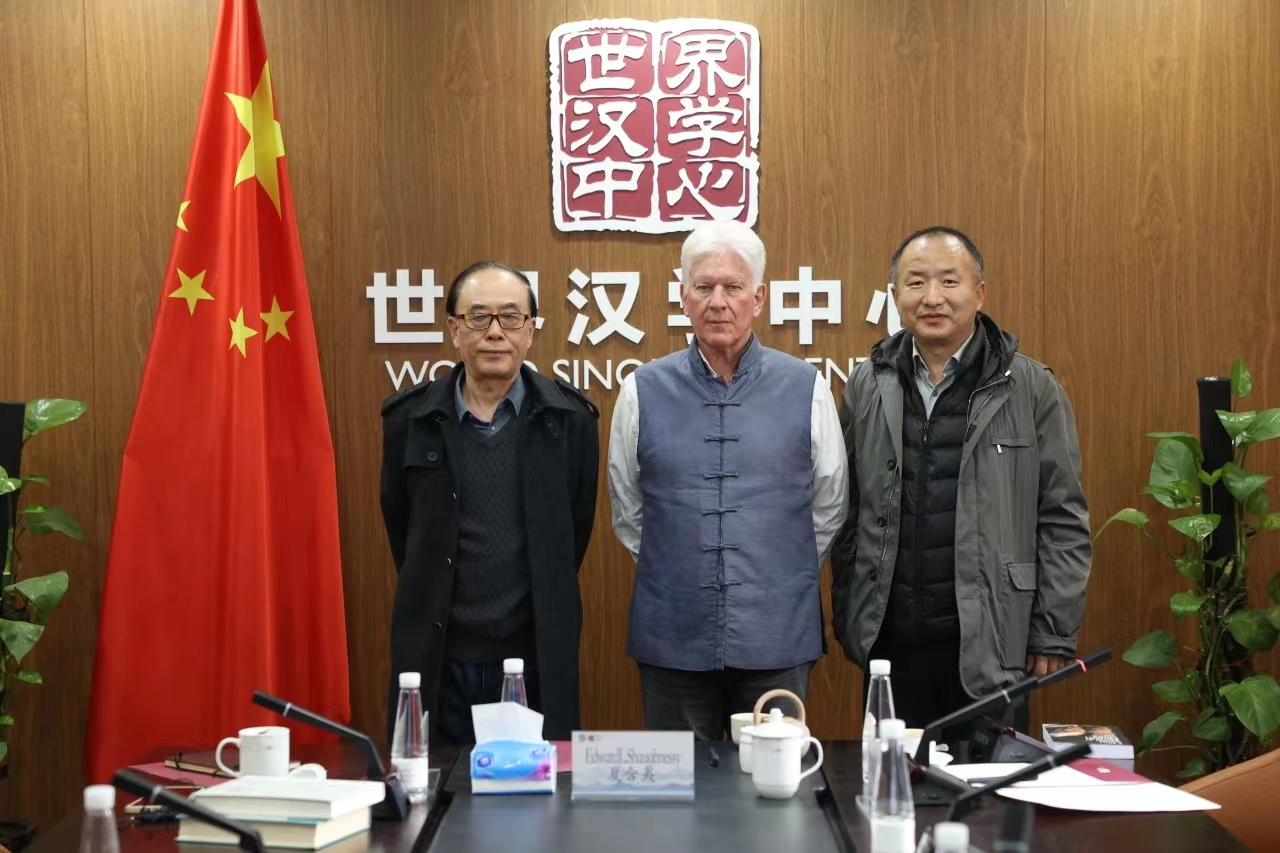黄卓越:“书写”之维:美国当代汉学的泛文论趋势
“书写”(writing),虽然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用语,但将之作为一理论命题予以聚焦性的阐述,进而在植入大量新的含义后被整合至当代主流知识话语之中,当首先归功于法国文化理论学派的工作。如早期学者巴特、德里达、德·赛都等均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书写”(écriture)做了超出常义之外的解释,并视之为是一种能够对思想史、观念史施予重大影响的编码活动。仅从以上述学者的论述来看,大致而言,至少包含有三种有所差异的思考方向,即一是将书写视为一种携有根源性意义的、形式化伦理的表征方式(巴特),二是用书写来对指与表音意识形态相区别、相对立的一种更具心灵自主性的文字铭记方式(德里达),三是将书写看作为被特定的方式组装起来,从而也会给外部世界秩序予以赋权的“神话”模式(德·赛都)。虽然这几个方面的用义有所不同,但又均在各自的论述中将书写这一概念涂抹上了鲜明的“文化政治”底色,这固然也与法国20世纪中叶伊始的理论走向有密切的关系。
与之相随,书写的概念被快速地接引至诸如民族志、后殖民等自反性研究之中,也渗入了此期在各领域中出现的向识字史、写作史、印刷史、阅读史、书籍史、翻译史等转向,及“物质文化研究”等的潮流中。以后者为例,像夏蒂埃(Roger Chartier)、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 罗萨琳德·托马斯(Rosalind Thomas)、亨利·马丁(Henri-Jesn Martin)、布莱恩·斯托克(Brian Stock)、沃尔特·奥恩(Walter Ong)等在对西方古典与中世纪等时期相关活动的历史考察中,便颇涉“书写”的概念,由此而渐次垦拓出了一新的话语实践空间。
就以上而言,尚能发现一从理论向历史锲入的步骤,以理论为先导,逐渐渗透到历史研究的多个分支领域中。而理论与历史的接合又形成了互为受益的效果,恰如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实所显示的,在理论神启式地点亮了历史的探寻之路时,历史也在大幅度地修订、充实、改编着理论的原样,并以持续扩延的方式为“书写”的概念填充入丰厚的含义。
正是受到以上趋势的影响,在当代英语世界,尤其是美国的汉学领域中,约自90年代初始,以“书写”为名的著述骤然增多,尤其是将这一概念挪用、结合到对中国传统文献与文本的考察中,试图借助于这一新的概念化工具来重新诠解中国文化构成的特征。相对于90年代以来随“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其他新的研究多会集中在晚期中华的历史变迁,以探索独特的现代性展开进程,汉学界对书写史的研究则多会偏向于以“早期中国”(Early China)为主要的论述区域,并试图凭借这一与西方世界有着较大差异的历史语境,从异文化的起源处来重新鉴别书写的功能与特点,扩充对书写含义的多样化认识。
当然,如从中国的传统表述来看,书写的概念其实早已有之,甚至于如泛义上的“文”也属书写概念中的题中之意,或倒过来看也一样,因此,也可就此意义上将之归入于文论史的论述范畴。书写研究与文论研究的关系,也可从“书写”与另一文论概念即“文本”之间难以驳分的关系中得到明证,因为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确无法脱离文本而讨论书写。关于这点,如在艾勃拉姆斯(M.H. Abrams)等所编纂的《文学术语辞典》(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中,便是将“text and writing”放置在同一个词条中来注解的,[1]这固然与近年来发生的学术变化有关,从而不仅印证了文本与书写两概念之间实际存在的某种孪生关系,进而也将文本化(textualization)看做是书写的一个操持过程与结果,从而打开了文本理论原有的设限,大幅度地更新了文本研究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书写,或为其带动的文本概念,也便具有了跨文类的属性,不再为狭义的“文学”概念所限定,而是也可为文化人类学、新史学等领域的研究所共享,[2]与之同时,对之的探索或理论描述也会与更具包容性的文化理论交融在了一起,进而导向一种泛文论的趋向。
从总体上的过程来看,在后知识语境下的书写与书写史研究,一方面会不断地征用各种当代文化理论,以扩展自己的话语容量;另一方面,在美国汉学中,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则是会相应地沿袭那些传统学科研究的轨迹,比如接续长期以来汉学领域中有关中西比较语言学、文字学等的研究,将传统文献学、注释学、版本学,当然也包括将狭义文学与狭义史学研究等学科发展中原有的议题兼容在内,进而通过将历史重新概念化的方式,引申出了一个新的,同时也是边界并不十分确定的学术话域。当这些研究被相应地簇拥在书写的概念之下,或机遇性地与书写的概念发生邂逅之时,我们似乎也看到了某种向“大汉学”回返的征兆。就特定的学科而言,在这一潮流的冲击之下,90年代之前奉行的那种狭义上的、专门化的中国文论研究,也被推入到一甚深的危机之中,逐渐地撤离到人们的视线之外。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有鉴于此,本文希望以此概念为聚焦的中心,从近年以来北美汉学中浮现的多种研究性材料中抽绎出若干近似的议题,并通过较为系统的梳理,呈现出在书写的名义或意识下所展开的各种新的努力。
一,“文本”与“权威”
从总的趋势来看,在书写或书写史的话域之中,尚很难确定是谁铲出了最初的一把新土,我们宁愿将之看做一个未曾闭合的、渐次性递进的过程。其中,尤其需要关注的还是传统学科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某些意识,有时也会为下一步的探索搭建出渡越的津梁。就较早的情况而言,值得一提的是鲍则岳(William G. Boltz)的研究。鲍则岳1994年出版了《中国书写体系的起源与早期的发展》(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一书,其标题已明确地将“书写”的概念囊括其中,尽管内文看似主要讨论汉字的早期情况,但其意图却是将汉字视为是书写的呈示方式来加以思考的,并非受限于传统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这项研究当然基于大量的实证性考察,但仍裹挟了一些明显的理论上的冲动,呈现出向新范式移进的痕迹。其中,至少有两个方向上的论述具有示范性的意义,一是汉字的书写属性究竟是否可归之于所谓的“表意性”(ideographic)范畴,从而可将这一在前殖民时期十分流行(至少可追溯至19世纪),并争论不休的命题重新置于后殖民的言说语境中加以重估?[3]这一命题的提出显然与德里达有无法撇清的关系,并包含有与后者论争的意图,进而也辐射到相继发生的一系列争论中,并与这些争论一起激发了从语言、字词等所谓的“语文学”(phiology)的角度重新考察汉语书写问题的热情。二是,也是更具启发意义的是,鲍则岳将汉语书写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置于秦汉时代,提出了秦汉时代其实是汉字,同时也是汉语书写被重构(reformation),进而被标准化(Standarization)的关键时期,其中如:“《说文解字》便是在秦始皇时期帝国的政治统一之后,由李斯所启动的为了使书写标准化而施行的正字法改革进程的终极成果。”[4]尽管还不能简单化地来看待这一问题,但汉字的标准化毕竟透露出了秦帝国所实施的各种统一化努力的一个基本方向,[5]由此而使这一重塑活动镌刻上了国家权力意志的鲜明属性。
对文本“权威”或权力作用的考察,在鲍氏后来的论述中也占据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且引起了汉学界对此问题的积极关注。在90年代最后几年内出现的两部著作,几乎不约而同地将“书写”与“权威”(Authority)的概念标示在其书名中,此即1998年出版的由康奈利(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撰写的《文本帝国:早期中华帝国的书写与权威》(The Empire of the Text: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1999年为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撰写并出版的《早期中国的书写与权威》(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为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此期书写史或泛文论研究的一种观念走向。
陆威仪90年代初撰有《早期中国的合法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一书,[6]提及战国时期发生的权威过渡或转换的问题,即所谓的“从弓箭到文本的历史”(the historicity of the move from bow and arrow to text),以为这是与从以世袭为基础的血缘契约而至以法律为约束的国家体制演化相一致的一个过程,从而导致了一种身体仪式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但是作者并未对“文本”的概念进行必要的分析、限定与展开。而此后,或当是受到新的学术理念的启发,陆威仪始将自己的研究聚焦于对文本演变与政治作用的关系上,随后出版的《早期中国的书写与权威》一书即是在此方面所做的一项较大规模的努力。陆威仪对研究的目标先有一个限定,即其关注的仅是在国家与社会层面上如何制造与运演权力的那些文本类型,在这一可控的范围内,去检测各种群体所扮演的角色。在他看来,目前西方有关书写与权力的理论,基本上都可用之于对战国时期“权威转换”(the transformation of authority)的观察中。通过对诸文本及其用义与功能等的探索,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书写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作用,便是在文本中创造出一个与之“平行的现实”(parallel realities),并声称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7]随着秦汉的国家统一,“前帝制时期”普遍信赖的征战原则与思想独立传统均遭到明显的削弱,书写的一致性至汉武帝时期达到了巅峰。从书写者身份位置的替换看,此时出现了一种兼有官僚与教师双重身份的、同时也是为体制所收编的一代新的精英,一方面是因为经济上的依附,另一方面也多少是出于内心的真诚,使得“国家”成为他们进行文本书写的最为权威与卓著的样式,而学术性的书写也始沦为一种财富与名望的机器。陆威仪的研究涉及多种文类,如行政文献、诗赋杂文、哲学论著、史学著述、政治散论、历法舆图、百科全书等,而这些也都可以用泛义的“文学”或“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的概念括述。[8]这一共名当然有独特的意义,除了含有对传统有关“文学”(“文”)概念的重新调用之外,更在于就作者看来,这些文类的体例尽管不一,然而却通过书写(“去自然化”)共同为构制出一个史无前例、包罗万象,并跨越多个世纪的“世界帝国”提供了一种想象性认知,同时这也是反事实性的模式。陆威仪最后还引用了博尔赫斯小说中关于“Uqbar”的描绘来说明他的寄意,即汉代书写所建构的这段历史就像在一部冒名的百科全书中才能查阅到的虚幻之地“乌克巴尔”一样,不过是一个假想性的“文本之梦”。[9]陆威仪的论说也隐在地涉及到了对文学与史学两种传统设定的书写边界的质疑,从而与其他一些学者在另一分支话题上所展开的问题串联到了一起。[10]另如史嘉柏(Daivd Schaberg)在其所撰的《模式化的过去:早期中国历史编纂学中的形式与思想》(A patterned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2001)及其他一些文章中,也阐发了类似的看法,并对早年汉学家在“抒情传统”研究中提出的直呈式结论提出了质疑。[11]
康奈利的著作,聚思于一种政治表象(representation)的构建方式。从其书中的叙述看,不仅涉及对西方当代书写史/文本史研究多种著述的评价,更涉及对多种后-理论资源的借鉴。其书名中措出的“权威”一语,按其所述,大致类似于“霸权”(霍尔)、“权力”(福柯)的概念,也可与“意识形态”(阿尔都塞)的概念相互替指,[12]甚至也可用“主体性”(subjectivity)的概念去附述之,而作者也是怀有这种高度的理论意识去谋划自己的著作的,故比之于陆威仪一书,会更多地在叙述中突显出被有意识地强化了的文论色彩。康奈利的研究同样集中在秦汉书写方式转型的问题之上,然仍与陆威仪主要从国家权力变更、政治身份移位的角度考察这一转型有所不同,康奈利更倾向于将文本书写看做是帝国权威构成的一个逆向性的动因。关于这点,著者认为可从多个角度加以论证。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作为书写介质的统一化,比如现在所说的“文言文”(literary Sinitic)便是秦汉帝国文化一体化政治的产物之一,除了字形以外,文言文也包含了一整套词汇、句法、文类(子类)等的规范性习则。很显然,文言文的词语并不是与现实体验所试图表达的对象相应的,然而其书写规则却预先提示了表达的内容与含义,因此而带有了法典性与强制性的效果。[13]尽管秦汉在大一统的威权格局中也保留了自战国时期延续而来的地方传统的多样性,比如存在着各种口语与方言,但是在书写语言之中,目前唯一能够发现使用的却仅仅是文言文。其次是汉代出现了为官方意志所主导的,同时也是高度发达的编辑系统(codified system),以致而使我们能够看到,在对经典的构造与意义的转化的背后,会存在着一套特定的叙述法则与特殊的意识形态,而其又以权威的方式指导着其他的各种书写活动(比如“纯文学”的书写[14])。从传播的视野上看,帝国的实践便常常地依赖于这种文本的循环,使得权威自身能够在这组文本转换的线路上被授权,并借此以造成一种“文本整体性”(totality of the textual)的效果。以同样的逻辑推断,汉代的“士”阶层虽然也可看做是社会地构成的,并是文本书写的主体,但是由于他们对文本官僚政体的隶属,因此还是应更合适地将之看做是文本政体(textual regime)的一种“效果”(effect)。[15]如此一来,在过去的文学研究中流行的所谓社会与政治对主体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张,便由于插入了一个新的中介,而发生了程序上的偏转,即更偏向于被认为是文本的权威(及生产这些文本的机制)构建出了作者的所谓主体性。与之相关,康奈利也会不断地去强调:“文本性并不是一个表征社会的工具,而是它自身便是表征的权威”,[16]因此而有必要超越传统认为的“它是那样”的解释,而取向一种“去自然化”(denaturalize)的解释。
上述学者聚焦的这一“权威”论题,还将在此后有关书写的其他研究中被不断触及。这些研究自然会依托于丰富的史料,所涉议题也不限于以上的简短绍述,但在这些颇富新见,并且也有重大开拓意义的论述中,也存在着一些无论是学理上还是实证上均难以牢固缝合的纰漏。康奈利与陆威仪的相通点,在于不管其曾经有过多少补充性的说明,均很明显地将“早期中国”做了“整体抽象主义”(totalizing abstractions)的架构,也就是从一种被整体打造过的理论假设出发去拢聚史实,并最终获取一种自我循环式的结论。就此而言,也可以将此类研究看做是后理论驱动下的一种结构主义尝试,或视之为是后殖民批评语境下所做的另类东方主义的冒险。此外,还有一些问题也需提出来辨明,即所谓的“文本帝国”的提法,将文本看做是权威建构的几乎是最为重要的介质。尽管,两汉时期的留存文本数量较大,与其他古老的文明的“废墟”性相比,中华文明依然有赖于它的“文本”性而始终能够保持历史记忆的延续性,[17]但是这些文本的实际流动状况,以致于影响权力塑形的作用并非就如上已述的那样简单。这是因为在纸张尚未发明,并主要是以竹木简为书写的物质前提状况下,备份(尤其是大的备份)的制作必然是十分困难的,加之大量书写文本更是仅为皇室所据有,或仅滞留在少数私人手中,以至于无法成为广泛传阅的读本。就目前所能发现的两汉时期的版本来看,许多的文本往往也只是留下了一或数个备份,而且多为后代所重新录制,这些都是在细致的研究与推论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与之相关,也需要再次重视口述在信息传递以及政治构型上的特殊意义,以免过度放大书写的功能。[18]
二,文类书写的特例:注释学研究
除了宏观方面的论讨,另有一些与书写相关或与书写史理念纠缠在一起的,同时也是更为具体化、分层化的研究也颇值关注,其一便是对“注释体”(注疏体,commentary, exegesis)/注释学的研究。注释学在当代频遭学界的亲睐,首先与解释学,进而是解构主义所提供的解读理论相关,因而从一开始就携有泛文论的色彩,并为那些企图以对传统古典学改造为己任的学者所追慕。而注释之所以也能置于书写的范畴之下,则是因为它与其他书写文本一样均基于同一种介质,甚至于往往被嵌入在正本书写之内,看做是正本书写的一个附属品,类于“副文本”的概念。过去对注释的研究多会偏重于论证其与正本之间的从属关系,因此也不甚将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类看待,而新的研究则多会有意识地去发现其与正文之间的缝隙与驳离,以及如何以另类书写的方式去移动经典的意义,从而大大增强了其作为文类的相对独立性(当然并非学科划分意义上的文类)。特别是书写概念的悄然引入,也使该项研究从过去只重视文本的含义,而开始转向对文本生产内在机制、施动策略等的探求,并赋予了这一模式某种文化政治的含义。
就一般对“注释”体例的关注来看,北美汉学界中对之的较早,并产生显著影响的一项研究可溯自如余宝琳80年代后期出版的《中国诗歌传统的意象解读》(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一书。进入90年代之后,又出现了范佐伦(Steven Van Zoeren)的《诗与人格:中国传统中的阅读,注释与阐释学》(Poetry and Personality: Reading,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1991)、韩德森(John B. Henderson)的《经文、正典和注释》(Scripture, Canon and Commentary:A Comparison of Confucian and Western Exegesis, 1991),以及苏源熙的《美学问题》(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 1993)等著作。而至世纪之交,则有如韩大伟(David B. Honey)所著《顶礼膜拜:汉学先驱与古典汉语文献学的发展》(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2001)、周启荣等所编撰的旨在从一长时期的历史阶段上阐述经典注释流动性的《想象的分界:变动中的儒家教义、文本与阐释学》(Imagining Boundaries: 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 Text, and Hermencutics,1999),[19] 涂经诒主编的从西方阐释学角度出发处理儒释道等经典解释的论文集《经典与解释:中国文化中的阐释学传统》(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2000), [20]余宝琳等随后编辑的试图参与对几种古典文本解读与注释的《文词之路:早期中国阅读文本的书写》(Ways with Words: Writing about Reading Texts from Eealy China,2000)[21]等,其后的研究则更有细化与扩大化的趋势。
从方法论视野上看,余宝琳早先的著作(对《毛诗》序注的阐述)还仅停留在一般注释学的研究上,尚未涉足更新的理论视野。范佐伦的著作则明确提出要用阐释学(hermeneutics)这一源自西方的文论概念来探讨中国传统的注释学,但又认为后者与西方早期至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所有阐释理论是有区别的,这也是由中国阐释学(或“经学”,“Classics studies”)自有的特点所决定的,因后者的核心是将“经典”视为一种具有普遍、终极意义的权威性文本,解读的目标是为了内化性地造就一种与经籍意义相一致的人格。以《诗经》解释学(尤其是毛诗学派的注释)为例,解经学的宗趣即体现在“诗言志”这一核心的表述上。具体而言,“志”是一个固定在文本中的,也是单一与不变的中心意义,而在另一方面,对之的解释又可能是丰富的,以及会随社会场景的变动而有异。[22]以此来看,虽然也需要关注意义的变动,然而中国注经学(批评学)中呈现出的理论意识又与“解构理论”(deconstructive theories)似无甚特别的关联。[23]
范佐伦之后,对注释学的研究始有更新的展开。韩德森的著作处理的是儒家经籍中的正典与注释之间的关系,尤其偏重于“注释是如何面向经典的”(how commentators approached the classics)[24]这一动态性的问题,特别是它们“制造”出了什么样的假设,以及是怎样处理其与经典文本所存在的冲突与矛盾等成分的。为了更有说服力地讨论这一问题,作者选取了中国儒家以外如印度吠檀多、犹太教、基督教(《圣经》)、希腊(荷马史诗)与回教等五个不同的正典与注释传统加以比较,认为其间存在着共同的基本假设与诠释策略,同时又因对这些假设与策略在应用方式上的差异而出现了分岔。[25]在作者看来,尽管注释会与原典之间存在着意义上的一致,但是几乎所有的注释又都会基于一种假设而介入到对经典的读解中,为此而也就必然会造成其与经典含义之间的某种驳离,而这也将是我们重新审视儒家经典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藉此可见,韩德森的研究显然已经比范佐伦了更递进了一步,即更强化注释学这一后续的活动所带来的对原初经典的解构性、间离性功效。既然注释活动是一种再书写,那么意义的延宕便会发生在文本间的传递与交接之处,为此而使原典的确定性无法着落,这与此期北美文学界在手抄本文化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也较相似。
苏源熙《美学问题》更为细致地涉及到对注释学撰述策略的思考。作者先是设定了一些明确的论辩对象,即集中于对90年代之前如余宝琳、宇文所安等对中西文论二元差异(真实与虚构,模仿与非模仿)的固化性解释的批评,并试图通过对“寓意”(allegory)这一间入概念的重新辨析,建立起一种新的跨文化理解的模式。苏源熙选取的主要文本是毛诗的评注(诗序与注释),并在一开始就表明其思路中携入了如保罗·德曼、雅克·德里达与杰弗里·哈特曼等解构主义大师的深刻影响,由此而不是沿过去的学术旧径,即总是试图通过寻找各种文本论据以求得一个真实与自然的“中国”,而是有意地避开对真实性的直询,去发现在那些文本书写过程中所使用的修辞手法与若隐若现的修辞策略,它们是如何决定了后来的人们对原典的理解的。在苏源熙看来,相对一个“自然”存在的文本观念,我们毋宁将这些评注视为是一种用“非自然”的方式去改变语义的“操作”(work),[26]也就是通过另类书写的方式去置换原有的意义。由此而再来看毛诗的评注,尽管后来的学者都以为其用特定的意识形态对《诗经》进行了过分的、同时也是不合原义的曲解,但是这在毛诗的评注者那里事实上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出在后来的人们如何看待其评注的态度上。以苏源熙的视角来看,注释的本义,具体而言即我们所说的毛诗的评注,其主要的目的正是要将原初的文本进行“主题化”的“操作”,并借助于新的书写路径去塑造一个守礼的理想之“王”,从而生产出一个具有合理化的“帝国”的概念。籍此之故,对注释或评注的判断就不应当局限于它离真实性有多大的距离,而是需要在将“言意”剥离开来的前提下,首先关注其是如何运用“寓意”等修辞性手法来达到诠释之效验的。继以毛诗的评注为例,其具有最终申诉权的便是作为“元美学”(meta-aesthetic)的“礼”, [27]这也是注释者在对经典原义加以改造的过程中特意插入的一个核心的观念部件。于此情况之下,作者所得出的结论也与陆威仪、康奈利等的论述是可贯通的(即文本权威的想象性建构)。而正是基于这种持续不断的对经典的重新注释,使得原典的意义(同时也像“中国”这样的意义)被不断地延宕,而不再像余宝琳、宇文所安、蒲安迪等文伦家所认为的,可以被固化在一个基础主义(也是二元对立)的概念上。
在此之后,苏源熙仍主要将中国传统书写与评注问题,包括早期汉学发生以来“他者”的评注史及汉语书写语文学(philology)作为其研究的聚焦点之一,出版了《话语的长城与文化中国的他者历验》(Great Walls of Discour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Cultural China, 2001)一书,[28]并与其他学者一起合编有《汉字字形:书写中国》(Sinographies: Writing China,2007)一书,[29]为此而形成一套较为成形化的有关中国书写的多层次研究的言述模式,并可与其时其他一些汉学家的在汉语书写史范围内所作的研究形成一种叉合性的呼应。
三,在“历史”中书写
以下的话题,几乎均被归在了由北美汉学界所发明的“早期中国”(Early China)这一带有“全史性”的学术命名中,以至于恰如柯马丁(Martin Kern)所述,由于近年来急剧加速的的学科跨域进程,使得要再明晰地区分原有的学科界限已很困难。以文学为例,“严格地说,可以游离于早期中国研究的体系之外,并且可以清楚界定的‘早期中国文学’是不存在的。”[30]此种说法当然也可用以替指在其他一些学科发生的状况,并也已为各种研究所证明。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命名之中,由于近来两种趋势的激发,已将“早期中国”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同时也是前程叵测的境地。这两种趋势,即一是中国考古学在最近几十年的重大发现,二是在另外一些领域如经典学、宗教学、圣经研究、近东研究与欧洲中世纪文学研究等之中所出现的国际研究新走向。[31]从前者看,中外学者之间多有沟通与交流,在欧美多国也均涌现出一批以简帛文献等为专治方向的学者。从后者看,汉学领域也明显地受到了当代西学各路研究的影响。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并于本命题相关的现象之一,便是围绕着“文本”这一概念所展开的多种探索。虽然“文本”的概念在这一确定层面上处理的首先也是一种“文献”,但是已不同于旧的文献学概念,而是同时也被转义为文论意义上的“文本”,即被看做是一个有所建构的对象。当然也不同于传统思想史、文学史等在进行内部自足式分析时所认定的意义载体,而是在被“书写”这一命题重新照亮与激活后的一个新的叙述范畴,因此而会更偏重于从符号生产与传播的方式、书写的物质前提、被书写注入与表征出的权力观念、书写的内在体式与规定性机制等视角对文本予以重新检审,由此而与泛义的文论研究联系在了一起。尽管“早期中国”研究所包容的范围要更宽泛一些,然贴近书写/文本话题所展开的各种研究却担当了一个“发掘机”的作用,以使各种理念上的创新能够在此沟渠中汇聚并有序地流出。这也涉及几个不同的面向,下文即选择性地介绍几例。
其一,是关于文本不确定性的讨论。如先不考虑受到更大氛围的理论启迪,大致主要涉及两方面的研究进展及从中得出的结论。首先是认为文本/文献在物质表现层面上即呈示出了一种不稳定性,这也是基于近20多年来地下文献的大规模发现,使得早期书写的本原状态或说是物质性得以比较充分地显露出来。经过中外学者的密集考订,已可充分地证明早期文本在抄写、编排等方面存在着诸种差异,进而也造成了文本表述的多样性与意义的流动不居。在我看来,这与早期书写条件的匮乏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意义的传递主要还是依赖于口头传播,而口头传播下来的文本又总是会因人而异的。除了手抄的方式以外,在当时也不存在着其他的书写手段,由此也使得每一次书写都必然是自我单元化的,以至于我们无法确证哪一文本是最初的,或最为可靠的。加之,在秦汉之前,汉字及其书写形式也未曾有任何标准化的规定,这也会使文献之间会呈现出微巨不同的异差。[32]
此外,文献体制的变化也会造成同一文本之间出现微妙或明显的差别。关于这一问题,一些汉学家认为既与秦汉时期对汉字的改型与统一有关,更与“西汉时期重塑中国书面文化传统的努力”有关,因此可以通过语文学体制的变化来探讨之。比如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等即认为西汉时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书写方式(文学书写抑或历史书写)即规范与决定了后人对上古史的理解,而这也应当与各类文士参与其中的、大一统的帝国文化规划有着潜在的关系。更有甚者,则因于刘向、刘歆父子对秘府文献的系统性重造(以今文重录,并删汰、改编原本,重新分目等),造成了一大批与原初文献面目大异的所谓“定本”,而我们后来所见的所谓先秦文献主要依据于此。[33]再如鲍则岳的研究,通过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各自结体方式的对比而指出,两者不仅字句与内容上有差异,而且其内部的构成秩序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早期的文本形态往往多由小的片段组成,在后来才以特定的方式及根据某种意图被组合在了一起,形成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这种“混成”(composite)式的集子,即“文学化的类散文式文本”(literary essay-like texts),或称为是经典集(classical corpus),又最后在向歆父子的重构性活动中以获定型。[34]也有学者通过具体某一文本的研究中,借助对地下发掘文献(郭店楚简与上博简)与现存《诗经》(毛诗)一些片段与引述的细致对比,认为在《诗经》被经典化以前,这一整体化的文本其实并不存在,文句与意义也因使用的差异而未曾确定化。[35]尽管近年来不同领域如文献学、考古学、文字学、文学史研究等方面的中外学者均参与了以上讨论,对大量的秦汉之前的文本均做了重新考订,然汉学家们的研究明显地在其中偏向于对文本及其意义做“不稳定性”(unstable)的解释,及企图将研究的结果做某种再理论化的尝试。如果考虑到在书写这一话题下英美学界存在的一个更大的语境,这一研究趋势自然也与文化理论的一般性讨论的进程具有步调上的一致性。
其二,是有关文本构型问题的研究。虽然在该名目下的研究几乎很难不留下结构主义等旧文论模式的影响,比如柯马丁在其精心结撰的《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in Shih-huang:Text and Ritual in Eealy Chinese Imperial Representation)一书中对石刻文本篇章所作的考析,即认为从对早期一批跨度较大的青铜铭文、石磬铭文以及秦王石刻铭文等的对比分析看,可以发现这些写作文本之间在韵律、修辞、用语、格式与意识形态等方面均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因此可判定该文类的内在的模式具有明显的因袭性特征,但是作者并没有将
- ·世界汉学讲坛 | 何广思教授解读中拉
- ·阿根廷何广思:超越西方范本才能获
- ·阿尤布: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
- ·黄卓越:早期中国的书写与汉学研究
- ·薪火永相传,著名汉学家马克林讲汉
- ·《人民日报》:《用翻译架起中葡文
- ·蔡宗齐(美国):开辟中国文化走向
11 月 22 日下午,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北京语言大学主办、世界汉学中心承办的世界汉学讲坛第九讲成功举办。本次讲坛由...
10 月 18 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
日前,由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牵头建设的土耳其汉学家理事会在青岛正式成立,土耳其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土耳其著...
摘要:该文原为作者2021年10月20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举办的一带一路汉学研究论坛上所做的现场演讲,对海外汉...
2023年6月7日下午,薪火永相传大师说汉学暨世界汉学讲坛第四讲成功举办。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
2023年02月0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7版刊登了《用翻译架起中葡文化交流的桥梁》一文。文章由新汉学计划海外高级中...
天下学问一家: 开辟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新路径 蔡宗齐 蔡宗齐(Zong-qiCai),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校区东亚语言文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