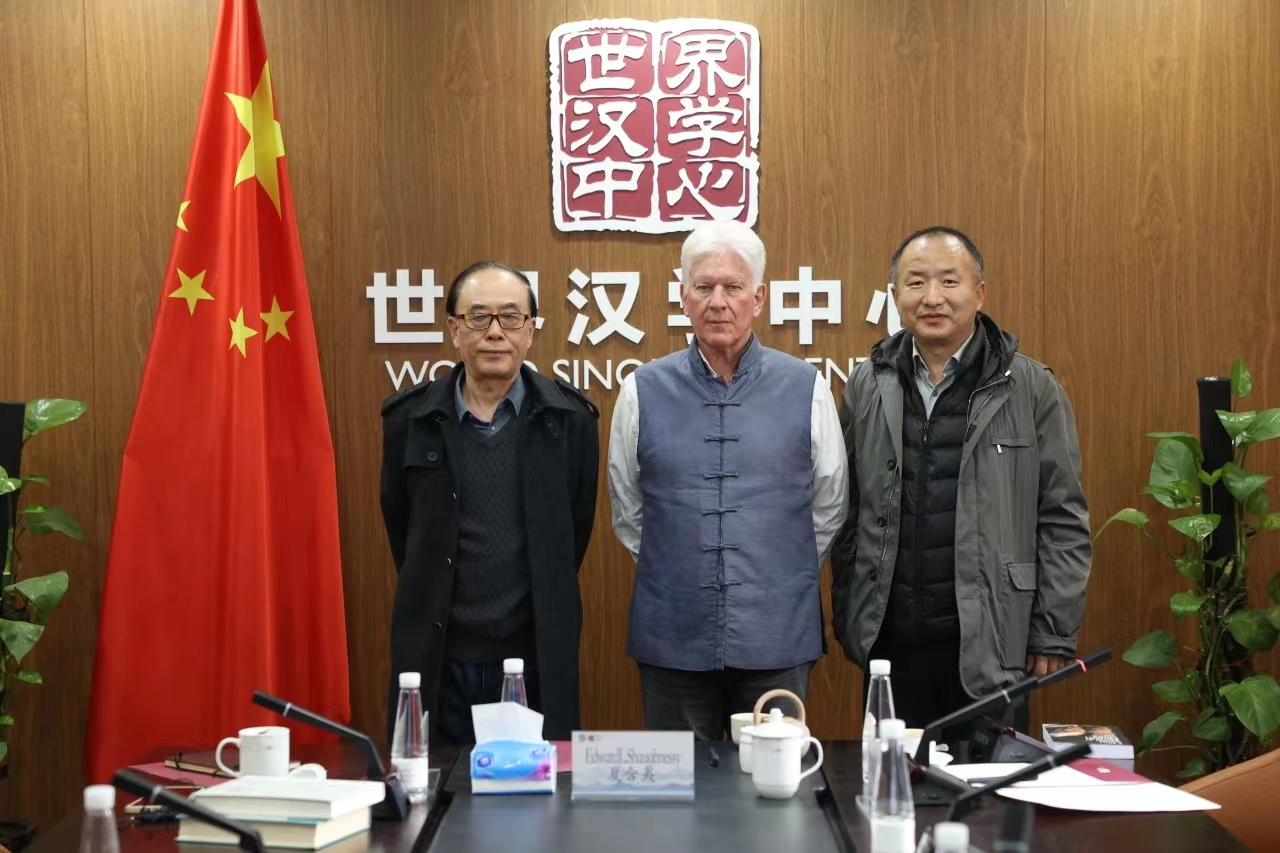方维规:汉学家对汉语结构的早期思考
语言与思辨——西方思想家和汉学家对汉语结构的早期思考
方维规

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其论著《哲学社会学:思想变迁的全球理论》[1]中发展了关于哲学体系之形成的全球理论,他在该著导论中介绍了四种在哲学或社会学文献中为人熟知的体系理论:(一)思想创造思想;(二)个体创造思想;(三)文化的自我生成;(四)一切都是变动的,不可能具有明确轮廓和明确解释。柯林斯试图与这四种理论保持距离,并以哲学在亚洲和西方的具体历史发展来阐释自己的观点。本文涉及的主要是柯林斯所说的文化的自我生成理论。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哲学产生于特定的文化场域,而文化场域具有句法标记,也就是不同语言的句式构造给不同文化打上了烙印。语言是所有认识论、本体论、逻辑思维得以产生的土壤,原因是句法决定了哲学表述的内容和形式。
本文所探讨的西方人对汉语结构和思维的早期思考,横跨四个世纪。时至20世纪中叶,西方学界对汉语与思维的关系问题的思考,见解可谓鲜明,然而一直处于探索阶段。并且,虽然相关论述似乎“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都是零散感语,专论并不多见。此乃“早期”之说的缘由。换言之,所谓“早期认识”,主要针对认识程度,而非时间概念。另须说明的是,中西初识之时,尽管在华“神父们撰写和翻译了大量的书,每天都在写作并将之译成中文”[2],但是当时还没有学科意义上的汉学家可言;这个语境里的“汉学家”只是一个宽泛概念。
1.“神秘”的汉语:一个历经三个世纪的悖论
李明(P. Louis Le Comte)在其《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中写道:“中国语言与目前世界通用的语言没有任何类似之处,无论在说话的声音上,在字的发音上,还是在概念的组合上,都无任何共同之处。在这一语言中,一切都是那么神秘。”[3]自有中西交往以来,汉语就是西人乐此不疲的一个话题。对于这一“神秘”语言,1582年奉派来中国的天主教耶酥会在华领袖利玛窦早就下过一个定论:“中文或许是所有语言中最模棱两可的了。”[4]“模棱两可”之说几乎是利玛窦之后所有同中国人打交道或研究汉语的西方人士的“共识”。对于汉语是否易懂易学的问题,则存在较大分歧。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在《中国新史》(1688)中说:“中国语言比希腊、拉丁或其他欧洲的语言都容易。[……]中国语言是所有语言中最简明的,它由三百二十个单音节组成,而希腊语和拉丁语则有无数的词、时态、语态、数、人称,等等。”[5]李明对安文思的这段文字感到吃惊,在他看来,“我不知很多传教士是否宁肯下矿井做苦工,也不愿数载如一日地辛辛苦苦致力于学中国话,这真是一个人所能经受的最苦、最易气馁的学习了。”[6]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西人当初在总体上对汉语的评价分歧。安思文说:“中国人使用的是五万四千四百零九个字,这些字表达他们要说的事,很优美、生动和有效,以致你不会把它们看做是字,而是说话的声音和语言,或者更是表示与他们生活有关的图画和形象。”[7]这只是当时的一种观点。对于“这数不尽的丑陋的图形”[8],当时还另有他说。此时,我们可以见到一种有趣的悖论:中国文字丰富多彩;中国文字资源不足。
一方面有人以为,虽然汉语方块字极为丰富,所表达的事物也各不相同,但是同用二十多个字母便能表达日常语言所有变化的欧洲语言相比,汉语中数不胜数、难以理解的符号甚至无法确定其读音、更不要说其真正含义了。“我起先以为中文是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语言,但随着我对它了解的增加,我发现从表现力来说,世上恐怕没有比它更贫乏的语言了。”[9]说其贫乏,主要是说汉字虽多,却没有足够的词汇来表述欧洲人所理解的各种事物、科学和艺术,尤其是哲学原理和宗教奥义。李明因此认为:“如果没有找到增加词义而不增加词汇量的办法,这数量不多的字的确是不够用的。”[10]另一方面,西人又赞赏“中国语言文字的力量和简练”,认为汉语“非常优美,非常丰富,极富表达力。因为它不需要词句去解释和阐明神学、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微妙和奥秘”[11]。
从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耶酥会士到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或其他西方人士,他们对汉语的认识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而且多半停留于“日常”的观察和“朴素”的认识。时至19世纪中叶,西方语言学家还宣称,掌握汉语需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12]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口语语言,可能也是希伯莱语之外最古老的书写语言。[13]令西方人沉迷却常常困惑不解的,依然是汉字这一在很大程度上从象形文字演化而来的表意文字。“随便解剖一个这样的汉字,你就会发现在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已经包含了它们组合之后所要表达的思想概念。那些古代中国的发明者们虽然成功地将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意识具体‘化’进了这些合成字当中,然而这些字所表达的内容往往很笼统,不够准确,甚至难以让人理解,荒诞可笑。”[14]
在20世纪之前的欧洲人眼里,汉语的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是其语法极其有限,没有规则可循。或许正是这“不足之处”,导致一种莫衷一是的现象:大部分人都把汉语看做一门最难学的语言,另有人却认为学习汉语几乎可以不费多大功夫,“可以在一年内学会,而且讲得很好。”[15]而这里体现的却是一个本质性分歧:一方面是多马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所说的汉语缺乏逻辑上的准确性,缺乏归纳和推理的语言表述。[16]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泰晤士报》记者柯克(George Wingrove Cooke)甚至宣称,汉语是世界上最复杂、最难懂、最笨拙的思维工具。[17]另一方面,利玛窦早就断言“中文当中并不缺乏成语和词汇来恰当地表述我们所有的科学术语”[18]。19世纪中期法国最重要的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在其专著《中国小说语言的句法》(1869/70)中指出,过去两千年的文献可以证明,汉语完全可以用来表达各种丰富的思想,中国人能够很有水平地探讨各种文学和科学问题。[19]不过,这种看法与当时盛行的观点格格不入。[20]
2.洪堡论“汉语精神”:不追求语法上的精确概念
每种语言都为思想和交流提供了基本模式,都有特定的规范,以调节思想和交流的程序。人们在运用一种语言时,几乎无法摆脱其特定规范。什么规范占据主导地位并融合于语言结构之中,这在不同语言之间可能存在很大差别。早在《马氏文通》问世前70余年,普通语言学的创始人、语言哲学奠基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于1826年3月20日在柏林科学院作了一个题为《论汉语的语法结构》[21]的报告,分析了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利弊。这个德文报告是洪堡研究汉语的成果;当然,报告中充满了他的语言哲学思想。在这之前,他已经在一封长信中把他的主要思想告知法国汉学家雷慕萨(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22]此人是西方“专业汉学”的创始人,1814年法兰西学院开设“汉文与鞑靼文、满文语言文学讲座”的第一任教授,重要著作有《汉文文法纲要:古文与官话纲要》(又名《汉文启蒙》)[23],该书是洪堡研究汉语的主要参考资料。在雷慕萨之前,关于汉语语法的书籍有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万济国(Francisco Varo)著《华语官话文法》[24],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著《汉语札记》[25],英国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著《中国言法》[26],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著《通用汉言之法》[27]等。洪堡关于汉语文言语法的论述,绝非全是他的独创,比如就当时的认识程度而言,马士曼的《中国言法》已经基本勾勒出汉语文言语法的概貌。洪堡的高妙之处在于其独特视角和语言哲学的理论高度。
就“语言与思辨”这个论题而言,尤其对汉语与西方语言的比较研究来说,洪堡的文章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从利玛窦到20世纪初(甚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人谈论的汉语自然是古代汉语,洪堡的相关比较研究也只能在这个框架之内。我们不能以《马氏文通》之后、尤其是后来发展起来的现代汉语来评判洪堡的一些说法。毫无疑问,从今天的立场来看,洪堡的一些语言哲学观点甚是绝对,不少看法也已过时;另外,许多古代汉语语法“规则”是《马氏文通》之前“不为人知”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洪堡对语言本质问题的锐利目光是不可否认的。他以独特的视角看到了其他人没有看到的问题,并对语言构造与思辨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洪堡看来,一部分词语从来就有主、谓、宾的意义,以表述独立的主体、各种特性或行为等。这种分类在不同的语言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借助它们以及与之相关的语法,人的思想才得以明确并获得明晰的表达。“语法比语言的任何其他部分都更隐蔽地存在于说话者的思维方式之中。”[28]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在语言中找到与思想匹配的表述。一个民族的语言精神(或曰语言共同体)必然作用于特定语法所造就的语言表述,即语言团体决定语法。“词的语法分类越细,语法表达的准确程度就越高。而词的分类则是由于对转化为语言的思想作了精确的分析之后才产生的,这一分析乃是语言作为‘思想的’官能所固有的功能。”[29]的确,现代语言学中的一个定论是:语法结构越是完整和明确,思想便更能在语言上得到精准的表达。没有语法形式的语言或语法不全的语言会妨碍智力活动的发展,这是由思维和言语的本质决定的。
洪堡考察的是汉语文言,将其与印度日尔曼语系的语言做比较,或者与欧洲的“古典语言”做比较。他看到了如下区别:与屈折语言不同,汉语没有变格、变位现象,单词是固定不变的,动词极少显示被动或主动。一句句子的意思完全取决于词义、词序和语境。在他看来,汉语因缺乏必要的字形标记而没有词类分别,或曰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词类和语法标记;词义及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决定其词性,真正的词类无从说起。汉语因词类标记不明亦即词法的缺席而只能构造简单句式,无法写出复杂的从句。
这似乎是最适合于汉语精神的方法。句子构造如此简单,当然是因为语法结构不容有其他类型的句子构造。[30]
洪堡认为“汉语在语法构造上几乎完全不同于一切已知的语言”[31],“在所有语言中,汉语文本的翻译最难再现原文特有的表现力和句子构造方式。”[32]在他看来,汉语句式呈现的是简单判断,只表明两个概念的对应或不对应关系,这种思维的原始逻辑形式类似于数学等式。而在印欧语言中,判断多半借助于不同概念的句法连接,动词作为谓语的主要成分在句子中具有中心意义。[33]中国人并不追求语法上的精确概念,[34]汉语是以别样的方式来呈现思想联系的,即“以简练、朴素、直接的方法呈现思想”[35],“以另一种方式引导着理解。”[36]因此,洪堡反对“把汉语同未开化民族拥有的语言混为一谈”[37],他非常推崇汉语
语法结构的纯粹性、规律性和一致性,这些优点无疑使它得以跻身世界上最完善的语言之列。但汉语与这些语言的区别又在于,它在人类语言的一般性质所允许的范围内,遵守了一个对立于这类语言的系统。[38]
洪堡认为汉语语法极不完善,“不过汉语即使如此也足以表达思想。”[39]他不排除汉语在形式上没有的东西可能存在于思想,一方面的缺失或许正是另一方面的优势。鉴于汉字字形不变、句子的含义来自词义本身、词的组合和前后顺序以及语境,他认为汉语的语言结构能够促进人对概念排序、大胆组合的乐趣。洪堡认为,在其他语言中相互关联的东西,在汉语里却往往孤立地存在着,从而使得汉语的词语或曰单个概念分量更重,迫使听者或读者仔细琢磨和咀嚼,在词义本身以及词序和语境中摸索词语与词语的关系及整体关系。因此,领悟含义就得下更大的工夫,语法的缺陷必须在理解过程中得到弥补,以真正把握句子和文本的整个含义。[40]另外,不管是在书面语言还是在口语中,汉语中的大量成语或惯用语可以满足中国人的一般理解需求并因此而无需费神。
然而,汉语特性使哲学思考充满模糊性,汉语语法也不关心这类问题。洪堡认为,这是中国人有意为之:“我们甚至可以说,汉语有时候对思想联系的标志不只是不加考虑,而是根本就不屑为之。”[41]可能有人会提出反驳,即中国人早就习惯于简单轻松的思维方式,语感会指引他们去辨别和把握词语的意义。但是洪堡不信此说。按照他的语言哲学,倘若中国人确实有着更强的表述需求,即尽量准确地描述思想关联,那么这会逼出相应的语言表达。“一种语法关系如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所青睐,就会在它的语言里获得相应的表达;反过来我们无疑也可以说:一个民族的语言如果缺乏某种语法关系的表达,就说明这种语法关系没有引起过它的注意。[……]凡是心灵中需要在语言上达到清晰明确的内容,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找到一个能够代表它的语言符号。”[42]
毋庸置疑,洪堡以及整个早期语言哲学更推崇印欧语言的语法、逻辑性及其功能。当时的西方学者基本上认为,汉语不能像西方语言那样完美地表达思想,也很难像西方语言那样达到不同凡响、令人称羡的高度个性化特色。然而,洪堡并不简单地认为一种语言的形式架构越是复杂,功能肯定越大。不过他明显注重书面语言的语法结构而忽略了表意文字或半表意文字本身所蕴含的超出文字的外部世界。他把汉语同数学等式相比较,显然忽略了汉字本身之不同于数学符号的内涵、情感因素和词义联想,以及大量文化背景。洪堡注意到汉字包括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和形声字,而恰恰是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一般包含超出文字本身的语义成分,指向文字以外的事物,亦即“超语言指称”(extra-linguistic reference)。如果洪堡言之有理,即形式上没有的东西可能存在于思想,那我们必须说,每种语言都需要某种程度的词类、语法或句法关系:这些关系网络在印欧语言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极为具体地体现于发音、文字或句式;而在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中,这种关系常常是暗含的、内在的。中国人看到“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样的诗句时,当然知道主语是谁,并不是西方学者曾经宣称的那样:中国人对主语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行为或事件,行为主体可有可无。(再重复一句,这里说的还是文言文和古代汉语。)
无论如何,耶酥会士对汉语的感性认识以及后来的传教士或早期学院派汉学家的“中国言法”知识,在洪堡那里才被上升到语言哲学的高度进行探讨。这时,我们才看到汉语是否适合于哲学和逻辑思维这个问题的提出。他的一些观点开风气之先,对后来西方世界的中西语言比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洪堡之后的一个典型的西方观点是,汉语因为汉字结构(单音节,字形不变等)而不太适合于抽象思维,更有利于直观的形象思维。换言之,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表意文字的汉字,不像西方的拼音文字那样,其含义多半已见之于文字符号。早期研究中国思想和语言的西方学者已经热衷于这类话题,并以此分析所谓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其语言比较的结论是:中国思维较多地带有审美和伦理色彩,缺乏的是理论性和思辨性。西方的逻辑思维主要借助句法上的组合,而表意文字或半表意文字使中国人推崇类比思维。中国古代哲人不擅长从抽象概念出发来进行演绎,而是喜欢用具体事例说明问题;他们不喜思辨,而以比照见长。此乃具体的、形象的思维。
3.模糊和悖谬vs.抽象和纯粹
洪堡之后,西人撰写的汉语语法书越出越多,[43]它们基本上都属于语法研究或实用课本。然而,关于汉语与中国思维的关系问题,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固定话题,或详或略地散见于各种中国概况、专论、述评、游记等文字。另外,在普通语言学或语言哲学中,汉语常是一个信手拈来的例子,用以与西方语言做比较。进入20世纪之后,关于中国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字和思想之关系的论述,典型地见之于法国大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的《中国人的思想》(1934)[44],作者是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和著名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学生。《中国人的思想》专用一章论述中国人的思想亦即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表达形式。
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语言看做象征之存在形式,它尤其是为了传达思想而被创造出来的。中国人则从来不把语言艺术视为与其他理解过程和施加影响的手段毫不相干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语言只是众多活动过程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设定个体在社会和宇宙所规定的秩序中的位置。[45]
葛兰言的描述是西方论述汉语及其文字的一个常见观点,即单音节的、不变格的汉字本身几乎没有伸缩性和变化性,其主要功能不是清晰地描述思想,更多地在于明白地、有分寸地表达诉求,语言的目的首先在于引发相应行为,明确的信息并非第一位的东西,重要的是对说话对象的行为产生影响。同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西方学者所代表的一个观点:汉语在逻辑思维上的短处,决不排除它在其他思想领域的功能。不少学者强调了汉语在社会政治思想和实用层面的能量,即中国思维的实用主义基本特色。另外,汉语在语言艺术尤其是诗歌中能够显现出巨大能量。葛兰言在论述中国字或词的时候写道:“汉字并不只是纯粹表达概念的符号,中国人并不追求使一个词尽量精准地达到一定程度的抽象性或概括性。汉字更多地是要让人意识到形象思维的整体,并强调整体中最活跃的成分。”[46]比如表示“老年人”的“耆”字,会引发一系列联想,这个词不只局限于一个概念,它还指向其他许多相关概念。词不只是抽象符号,它能唤起特定情感以及与之相配的行为。汉语词是多层次的,其特定标记使之获得多重维度。因此,葛兰言认为中国人思想中的词语标记比欧洲人之文化认识中的标记丰富得多。关于一个人的“死亡”,中国人可以通过不同的表达死亡的选词来表达对死者或褒或贬的评价。
关于汉语风格的一种西方传统论说亦见之于葛兰言的著述,即中国哲人喜于阐释一些老少皆知的典故,这些典故出现在不同的著作中,但是诠释各不相同。这种特殊风格缘于这些哲人不愿直言其意图,故而借用典故。这种形式的哲学论说的优势是,它能激发幻想,用叙说的表现力来影响读者。它不追求激发读者对哲理的分析性思考和判断,思路在逻辑上的准确性不是关键问题,重要的是整个叙述的启发性。葛兰言对汉语与中国思维之关系的思考,一方面可以让人看到他对前人论说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涉及西方学界的一个“古老”问题:汉语是否与西方语言一样适合于逻辑思维,或者不太适合于逻辑思维?换言之,汉语的语言结构在形式上是否能同西方语言一样方便地连接各种思想并建立逻辑体系?
葛兰言的同时代人、著名德国汉学家佛尔克(Alfred Forke, 1867-1944)在其论著《中国文化圈的思想世界》(1927)[47]的第四章论述汉语之哲学意义时,也探讨了汉语结构对哲学思考的影响。一方面,他认为汉字“几乎总是同具体事物连在一起,能够促进具体的形象思维”[48]。另一方面,他从汉字的多义性(即一个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及由此而改变的词性)出发,指出汉语词义的模糊性:
人们必须要从一个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及语境中挖掘其真实含义。时常是多种完全不同的含义才真正显示出意义。因此,有时对一句句子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理解,注释者会做出相去甚远的诠释,翻译中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用汉语明确地表达思想。然而,中国人一般都很重视文章的典雅,其程度远远超过对清晰性的追求。这便形成一种极为简洁、讲究辞藻的风格。于是,为了达到不同句子之间的华丽的对照或对仗效果,中国人甚至全然不顾逻辑上的悖谬。对中国哲人、尤其是古代哲人来说,借助抽象概念进行理性演绎是不可取的。他们宁可用恰当的情景来表达思想,可想而知,这常常会导致不同的解读。故此,中国人自己对古代哲学文本的理解也不是容易的事,在有些情况下,不看注疏几乎不可能读懂。
- 上一篇:铁说红楼: 《红楼梦》的腰在何处?
- 下一篇:大范甘迪
- ·世界汉学讲坛 | 何广思教授解读中拉
- ·阿根廷何广思:超越西方范本才能获
- ·阿尤布: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
- ·黄卓越:早期中国的书写与汉学研究
- ·薪火永相传,著名汉学家马克林讲汉
- ·《人民日报》:《用翻译架起中葡文
- ·蔡宗齐(美国):开辟中国文化走向
11 月 22 日下午,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北京语言大学主办、世界汉学中心承办的世界汉学讲坛第九讲成功举办。本次讲坛由...
10 月 18 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
日前,由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牵头建设的土耳其汉学家理事会在青岛正式成立,土耳其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土耳其著...
摘要:该文原为作者2021年10月20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举办的一带一路汉学研究论坛上所做的现场演讲,对海外汉...
2023年6月7日下午,薪火永相传大师说汉学暨世界汉学讲坛第四讲成功举办。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
2023年02月0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7版刊登了《用翻译架起中葡文化交流的桥梁》一文。文章由新汉学计划海外高级中...
天下学问一家: 开辟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新路径 蔡宗齐 蔡宗齐(Zong-qiCai),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校区东亚语言文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