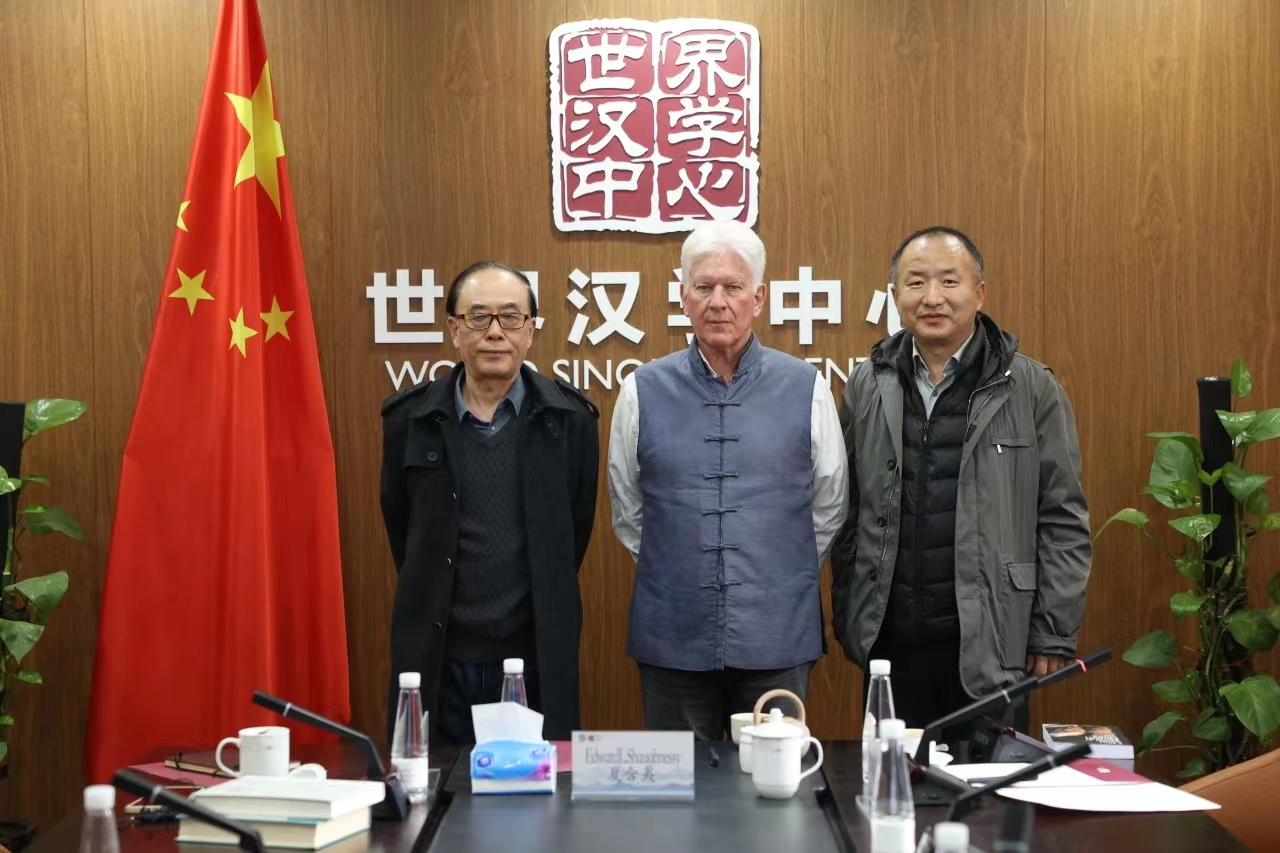任增强:“媒、讹、化”与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
来源:译研网 作者:无 时间:2014-11-20 21:57
“媒、讹、化”与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
任增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55)
(北京语言大学 汉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3)
[摘要]《聊斋志异》在国外流传甚广,其中翟理斯之英译是《聊斋志异》翻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以钱钟书关于翻译的“媒”、“讹”、“化”之说加以烛照,可周衍地发明翟氏英译的特色。其中,“媒”表征于翟氏译本注释,起着有效传递中国文化媒介之作用;“讹”体现为翟氏出于纯洁化之考量而对原作性描写所作的置换与删节;“化”落实为两个层面,译文恰如其分地传递出原文洗练优美的文风、译文所觅取文化意象与原文中的文化意象间形神兼似。
[关键词]翟理斯;《聊斋志异》;钱钟书;译论;翻译特色
《聊斋志异》以其洗练优美的风格与丰富深邃的意涵,不仅在中国国内家喻户晓,而且被翻译为别国文字,在诸多国家广为传布,是中国古典小说中被翻译为外文最多的一部小说。从传播时间上看,《聊斋志异》首先在18世纪下半叶传入东方国家,其后则于19世纪中期流入西方国家;从形式上看,《聊斋志异》在海外的流布可分为单篇译文和译本两种。其中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的英文节译本《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共译《考城隍》、《种梨》、《劳山道士》、《瞳仁语》、《莲香》、《汪士秀》、《毛狐》、《雷曹》、《酒友》、《陈云栖》等164篇作品,其中149篇是此前未曾译为英文的,乃最早颇具规模的译本。
更值一表的是,翟理斯译本以其独特之魅力,被转译成多国文字,在西方世界代表蒲松龄达一个世纪之久。翟氏《聊斋志异》英译本之特色已有学者进行阐发,但多是借助于西方翻译理论予以解析,往往单从某一维度出发,各照隅隙。而以钱钟书先生独具中国特色的译论加以烛照,大可擘肌分理,剖析毫厘,更为周衍地发明翟氏译本的翻译特色。钱先生曾独辟蹊径,对翻译之“译”字从训诂学角度做出阐析,指出《说文解字》卷六《》部第二十六字:化,译也。从,“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化”,读若“诱”。意为“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讹”、“化”和“化”是同一个字。“译”、“诱”、“媒”、“讹”、“化”实际上是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①]
参酌钱钟书先生的相关论点,本文以“媒”、“讹”、“化”为切入点对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之特色加以厘定,并枚举著例予以剖示。其中,“媒”表征为翟氏译本的注释,翟氏借助注释客观公允地绍介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英语世界读者接受中国文学作品,进而了解古老的中华文明发挥了媒介的作用;“讹”即意指译文与原文不相符合、不忠实于原文。具体至翟氏英译,则体现为译者为求净化与纯化对原作中性描写内容的置换与删节。此举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原作精神内涵的流失;“化”,指的是翟氏译文将《聊斋志异》由汉语转换为英文,既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之痕迹,又能保存原作的风味。具体而言,“化”一方面体现在语言层面上。翟氏译文语言与原文自然、不隔,恰如其分地传递出原文洗练优美之风格;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文化意象。翟氏译文所觅取的西方文化意象与原文里的中国文化意象形神兼似。
一、媒:作为文化传递媒介之注释
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的一大显著特色便是译释并举。翻译非但是不同文字之间的转换,更是对他者文化信息的传递。可以说,以《聊斋志异》译本来展示中国的一般情况,是翟氏英译的一大特色。翟氏翻译《聊斋志异》之目的即是为了让西人经由中国文学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并借以消除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的曲解。在其首版英译《聊斋志异》导言中,翟氏便明确指出自己的翻译目的“一则可以使西人更加关注中国;另一方面,至少能够纠正一些错误的观念。某些平庸而狡黠的作者经常不诚实地把一些谬误灌输给读者, 而读者也习惯于不加思考地照单全收……结果是,许多中国习俗不断遭到揶揄和贬斥,究其原委不外乎是传递者扭曲了中国的形象。在这部作品中, 通过一位学殖深厚的作者对其国人和国家的确切书写,我们可以发现大量中国人在宗教和社会生活方面所真正信仰与奉行的东西”。[②]
翟理斯上述所言绝非空穴来风。西方世界早期的《聊斋志异》译介者,如德国传教士郭实腊 (Charles Gutzlaff)、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便曾从狭隘的宗教一元论立场出发,认为《聊斋志异》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宣扬异教信仰的宗教读物,其中反映的道家思想具有浓厚的鬼神迷信色彩;中国人的信仰是偶像崇拜,他们认为恶魔和幽灵充塞了整个世界,并用香火与冥币加以祭拜;还将英雄或者圣人加以神化,将其灵魂与幽灵、鬼怪等物同等看待。[③]此种情况表明,西人对《聊斋志异》的味趣在传教士汉学阶段已开始萌生,但是传教士汉学家缺乏对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真正了解,加之出于传播福音的宗教目的,郭、卫二人便对《聊斋志异》加以诋毁与曲解。精审而客观的学术研究还须留待专业汉学家加以完成。
翟理斯便是可以担纲的专业汉学家。翟氏在华长达二十五年之久,谙熟中国语言文化,“对汉语语法结构有着精准之认知,并且对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信仰与一般社会生活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洞悉”。[④]正是在其不懈努力下,《聊斋志异》及中国文化在西方的流播才开出新局面。
翟氏在翻译《聊斋志异》时甚为注重通过注释来传递中国文化,在其所译的每则故事后一一下注,附上一些供英语读者理解而不可或缺的注释,对西方人有关中国文化(比如道家思想)的曲解起到了纠偏的积极作用。在此不妨一观翟氏在随文注释中对中国道教的表述:
“关壮缪”(the God of War):中国的战神(the Chinese Mars),一位声名显赫的战士,名为关羽,约生活在公元3世纪初。死后被尊为神,供奉在庙中。”(《考城隍》注释4);“道教,有时亦被视作理性主义,为公元前6世纪名为老子之人所创。‘老子’意即‘老成的孩子’,据说老子出生时须发皆白。道教最初是纯粹的形上体系,如今只有先前的一点影子,多为来自佛教粗陋的迷信形式所影响,当然佛教亦吸收了道教的诸多形式与教义,二者汇融,殊难区分。据说道士会炼金术和玄门法术。”(《种梨》注释1);“有人认为道士炼有琼浆样的长生药(外丹),另一些人以为仙丹只有通过自身修炼方得炼成(内丹)。”(《劳山道士》注释1);“道士通常被认为具有某种特殊法力,能够让剪出的纸人、动物等变活,并用它们来做好事或者坏事。”(《妖术》注释5);“每一位道士都有一把宝剑,类似于西方巫师的魔杖。”(《成仙》注释8)。[⑤]
此外,有关古代中国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的注释:
“清明(the spring festival of clear weather):二十四节气之一,在每年的4月5日左右。这天需往祖坟上祭奠先人。”(《瞳人语》注释1);“乞丐行讨的方式(To call attention to his presence):乞丐为了能讨得施舍,要么在店铺里大声敲锣,干扰店主做买卖;要么是把动物的死尸绑在木棍上,拿着在店里摇来晃去。”(《道士》注释2);“关于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更(watch):中国古代打更的计时法,把夜间分为五更。相当于现代的晚上7点到9点为一更,9点到11点为二更,午夜11点到1点为三更,凌晨1点到3点为四更,凌晨3点到5点为五更。每一更,打更人打五下木锣。”(《三仙》注释2)[⑥]
由上述诸例可见,翟理斯之注解不同于郭实腊、卫三畏等人带有文化沙文主义的褊狭诠释。作为专业汉学家,翟氏叙述较为冷静中立,更具有学者的严肃性与公正性,基本摆脱了早期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偏见,以“理解之同情”(陈寅恪)、“温情与敬意”(钱穆)体认中国传统文化。在此,翟氏借助于注释非但对先前传教士汉学家加诸道教的种种曲解有所澄清,而且充分发挥注释媒介之功用,通过随文所下的逐条注释将《聊斋志异》正文中不易于西方读者理解的民间信仰、节气时令、生活习俗等相关文化内容更为客观、详实与通俗地加以绍介,借以消弭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在西人正确评价中国和中国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⑦]帮助西方读者对古老中国有了近距离的了解与认知,进而有效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西播。
二、讹:对原文的净化处理
“讹”可理解为译文与原文不相符合、不忠实于原文。具体至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本,“讹”体现为翟氏对原文的净化,即是说,出于纯洁化之考量对原作性描写内容的置换与删节,不妨观几个实例。
原文:马疑其迷途,顾四野无人,戏挑之。妇亦微纳。欲与野合。笑曰:“青天白日,宁宜为此。子归,掩门相候,昏夜我当至。”马不信,妇矢之。马乃以门户相背具告之,妇乃去。夜分,果至,遂相悦爱。觉其肤肌嫩甚;火之,肤赤薄如婴儿,细毛遍体,异之。又疑其踪迹无据,自念得非狐耶?遂戏相诘。妇亦自认不讳。(《毛狐》)
该句表述的男女调情淫奔之事,其中不乏狎昵的动作。但翟理斯却进行了改写:
“Ma concluded she must have lost her way, and began to make some playful remarks in consequence. ‘You go along home,’ cried the young lady, ‘and I’ll be with you by-and-by.’ Ma doubted this rather extraordinary promise, but she vowed and declared she would not break her word; and then Ma went off, telling her that his front door faced the north, etc., etc. In the evening the young lady arrived, and then Ma saw that her hands and face were covered with fine hair, which made him suspect at once she was a fox. She did not deny the accusation.”[⑧]
翟理斯的译文回译为汉语即:马天荣意识到她一定是迷路了,于是拿些话来打趣。“你先回家,”少女说道,“我很快便来找你。”马天荣不相信,少女发誓说定不食言;马天荣走前告诉她家门朝北等等。到了晚上,少女果然来了,马天荣见她手上脸上都长着细毛,怀疑她是狐狸精。少女也不否认。
在此,原文中的“顾四野无人,戏挑之。妇亦微纳。欲与野合”、“青天白日,宁宜为此”等充满性挑逗性的语句被置换,代之以“于是拿些话来打趣”、“你先回家”。而原文中“夜分,果至,遂相悦爱。觉其肤肌嫩甚;火之,肤赤薄如婴儿,细毛遍体,异之”等描写马天荣与狐女肌肤之亲的句子,则被替换为“她手上脸上都长着细毛”,其余关乎性与女性身体的描写一概被剔除殆尽。
至于在不妨碍译文流畅与连贯性的情况下,翟氏则干脆进行零度翻译,对原文中其以为不雅的成分直接加以删减。
如:问:“何需?”曰:“樱口中一点香唾耳。我一丸进,烦接口而唾之。”李晕生颐颊,俯首转侧而视其履。莲戏曰:“妹所得意惟履耳。”李益惭,俯仰若无所容。莲曰:“此平时熟技,今何吝焉?”遂以丸纳生物,转促逼之。李不得已,唾之。莲曰:“再!”又唾之。凡三四唾,丸已下咽。少见,腹殷然如雷鸣。复纳一丸,自乃接唇而布以气。生觉丹田火热,精神焕发。莲曰:“愈矣!”(《莲香》)
翟理斯对该段的翻译异常简洁,删去了其中的大多数细节,将之译为:
Miss Li did as she was told, and put the pills Lien-hsiang gave her one after another into Sang’s mouth. They burnt his inside like fire; but soon vitality began to return, and Lien-hsiang cried out, “He is cured!”[⑨]
翟氏的译文回译为现代汉语即:李女按照莲香所示,将药丸一一放入桑晓口中。桑晓只觉得丹田火热,很快便恢复了元气。莲香喊道:“他活过来了!”
如此删节,行文故也流畅,但原文中男女亲昵之动作描写荡然无存。其他如《夜叉国》中徐生与女夜叉交媾之“雌自开其股就徐,徐乃与交。雌大欢悦”;《陈云栖》中女道士非礼真毓生之“两人代裸之,迭就淫焉。终夜不堪其扰”;《阿霞》一文中男女欢爱之“既归,挑灯审视,丰韵殊绝。大悦,欲乱之”、“入以游词,笑不甚拒,遂与寝处”、“夜果复来,欢爱綦笃”;《聂小倩》一文中,表现女性冲破封建礼教的大胆表白之“月夜不寐,愿修燕好”、“夜无人知”等语亦是完全被剔除了。
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优美而雅驯,译作亦如译者本人颇具绅士风度,但为求净化而对原作中有关性描写内容的大肆“阉割”,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原文所表达思想内涵的流失。此可视为翟译美中不足之处。翟氏生活在英国的维多利亚王朝时代(1832-1902),彼时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但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尚未得以完全清除。资产阶级在婚姻观念上抱残守缺,认为婚姻是上帝对那些遵守社会传统道德习俗的人的恩赐与褒奖,要求妇女婚前必须是处女,女子失去贞操,就沦为道德堕落的人。翟理斯的英译自然难以脱离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出于性道德洁癖,翟氏对《聊斋志异》中涉及青年男女私情幽媾之事剔除得一干二净,使其译本俨然又好像一本少儿读物(翟理斯在该译本寄语中,便提到“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与孩子们”)。但这种“阉割”与“净化”显然有损原意,无法体现原作者蒲松龄作为落魄书生寻求精神慰藉的渴望,以及原故事所蕴含的追求恋爱自由与思想解放的时代意义。可以说,在此一点上,囿于时代的道德观念,翟译未能进入原著的精神世界。但对《聊斋志异》洗练优美的语言与其中文化意象的处理上,翟理斯的译文堪称是达及“化”的境地。
三:化:语言与文化意象的翻译
“化”,是翟理斯英译《聊斋志异》的又一特色。《荀子·正名》中说,“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⑩] 此种解释表明“化”,即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时,内涵意义与精神风味不变。如有论者所指出的,翟理斯的译文是以欧洲语言之肉身展现中国文学的精神。[11]与原文相参,翟氏英译《聊斋志异》之“化”具体落实于两个层面:一是语言,二是文化意象。
翟理斯由于长期浸淫于中国文化和文字,能够辨识蒲松龄的写作风格,欣赏其洗练优美的语言,并在译文中加以传达。翟氏认为蒲松龄“文风纯真而优美”(purity and beauty of style),且在《聊斋志异》中将“简练风格发展到了极致”(terseness is pushed to its extreme limits),[12]翟氏对自己的译文也追求洗练优美的风格。
简洁是蒲松龄语言一大特点,如《雷曹》中“乐云鹤、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长同斋,相交莫逆”一句,蒲松龄采用连动句式,“少同里”、“长同斋”、“相交莫逆”连续性的谓语描述出了历时的变化,区区数语便将人物间由幼时至成年后的关系交代清楚。然而,连谓句在英语中却结构松散,表现力弱,因此,翟理斯将之译为:
“Le Yun-hao and Hsia P'ing-tzu lived as boys in the same village, and when they grew up read with the same tutor, becoming the firmest of friends.”[13]
在此,翟氏以时间状语从句和分词结构来翻译原文中的连谓句,使译文达到了同样简练、紧凑的艺术效果。
除用语洗练外,蒲松龄的文笔甚为优美。如《汪士秀》中描写蹴鞠的一段话,用笔极为生动,具有形象美、动态美与音乐美的特点:“踏猛似破,腾寻丈;中有漏光,下射如虹;蚩然疾落,又如经天之彗;直投水中,滚滚作沸泡声而灭。”翟氏译作:
“It seemed unusually light and soft to the touch, and his foot broke right through. Away went the ball to a good height, pouring forth a stream of light like a rainbow from the hole Wang had made, and making as it fell a curve like that of a comet rushing across the sky. Down it glided into the water, where it fizzed a moment and then went out.”[14]
译文亦达到了传神的审美效果,同样激起视觉、听觉上的美感。首先,在原文中,蒲松龄用生动的比喻来描写汪士秀高超的蹴鞠技艺,“下射如虹”、“如经天之彗”,想象十分新奇,比喻也非常妥帖。翟理斯则将之译作“pouring forth a stream of light like a rainbow from the hole”(如彩虹般从孔中倾射出一束光芒)与“it fell a curve like that of a comet rushing across the sky”(如彗星划过天际,曲线形落下),以此来描绘蹴鞠在半空中及落水时的生动画面,均充分传达了原文的形象美。其二,原文用“腾寻丈”和“直投水中”来表现蹴鞠被踢出时的动感,翟氏则以 “Away went the ball to a good height”、“Down it glided into the water”加以对译,用副词“away”(离开)和“down”(往下)前置的句式突出展现动态美。至于原文中的声音,“滚滚作沸泡声”在翟氏译文中被译作“fizzed”(作嘶嘶声),更直接呈示出逼真的音响效果,充分再现了原句的音乐美。
由上述两例可见,翟理斯深刻体察蒲松龄语言的特色,充分发挥译语优势,在译文中以自然、流畅而贴切的英语,充分再现原文凝练优美的语言风格。
进而言之,翻译非但是两种语言符号系统的转换过程,亦是两种文化体系间的碰撞。除语言层面外,在对文化意象的处理上,翟氏的英译与原文也可谓形神兼备,达及“化”的境地。
如:生意友人之复戏也,启门延入,则倾国之姝。(《莲香》)
And Sang, thinking his friend were at their old tricks, opened it at once, and asked her to walk in. She did so; and he beheld to his astonishment a perfect Helen for beauty. [15]
翟理斯将中国文化中指称美人的“倾国之姝”译为“绝色海伦”(a perfect Helen for beauty),而海伦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女。“倾国之姝”与“海伦 ”均用以泛指美女,作为不同的中西文化符号而有着相通的所指。
再如:生曰:“我癖于曲蘖,而人以为痴;卿,我鲍叔也,如不见疑,当为糟丘之良友。(《酒友》)
“Oh,” replied Ch’e, “I am not averse to liquor myself; in fact they say I’m too much given to it. You shall play Pythias to my Damon; and if you have no objection, we’ll be a pair of bottle-and-glass chums.”[16]
原文中的“管仲”、“鲍叔牙”,均为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鲍叔牙知人,举荐管仲。“管鲍之交”的故事一直作为美谈,传流后世。文中借用此历史典故,旨在形容车生与狐狸友情之莫逆。翟理斯用“Pythias”(皮西厄斯)和“Damon”(达蒙)来对译原文中出现的“鲍叔牙”和“管仲”。而皮西厄斯和达蒙乃古罗马民间传说中友谊的典范。皮西厄斯被国王判处死刑,达蒙为了让其友回家清理家务而代他入狱。后正当处死达蒙之际,皮西厄斯归来,国王被他们的信义感动,宽恕了他们俩。如此用西方友谊之范例加以对译,可谓形神兼备。
又如:白顾梁曰:“吾等面薄,不能劝饮。汝往曳陈婢来,便道潘郎待妙常以久。”《陈云栖》
“The gentleman won't condescend to drink with us,” said Miss Pai to Miss Lianp,” so you had better call in Yiin-ch'i, and tell the fair Elo'isa that her Abelard is awaiting her.”[17]
“潘郎与妙常”的典故出自明代高濂所著传奇《玉簪记》,讲述的是道姑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的爱情婚姻故事。文中用作双关语,借指陈云栖与真毓生的情人关系。而翟理斯将之译为“Abelard”(阿伯拉尔)和“Eloisa”(爱洛伊斯)。阿伯拉尔,中世纪法国神学家和哲学家。他与学生爱洛伊斯颇赋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曾一度风靡欧洲,二人的名字也与“潘郎与妙常”一样成为情人的代名词。
由上述诸例可见:首先,翟理斯以其对来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符号系统各自结构特征的熟稔,以典故来对译典故,在形式上实现二者间的妙合无垠;其次,翟氏以敏锐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深刻体悟原文的表达方式与源语典故的意义内涵,继而觅取西方文化中近似等值的文化意象,从而使得译文与原文所生成的文化联想具有了同一指向,使译文对译文读者产生原文对原文读者相同或相近的语用效果,心领神会、灵犀点通。如此,实现译文与原文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形与神的融合,故而达及“化”的境地。
概而观之,以钱钟书先生“媒”、“讹”、“化”为视阈,可较为全面地发明出翟译《聊斋志异》的翻译特色。翟理斯以详实而实用的注释为媒介,客观地向西人绍介中国的传统文化;又“以美和内涵取代了前人粗俗的译笔”,[18]有效地传递出原文洗练优美的艺术风格,传达出原作的内在气度,展示出汉籍《聊斋志异》的卓越丰姿。但从另一方面观之,翟译并非完美无缺,由于受制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念,译文中多出现讹变之处,致使在阐发原作精神内涵方面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定的局限。然而,翟译的成败得失为后来的《聊斋志异》翻译提供了参考与借鉴,作为汉籍英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即使翟理斯教授只留下此一本译著,我们也要向他致以永久的谢忱”。[19]
滚动新闻/Rolling news
·从”龙“的翻译变化看中文外译新时代发展
·张西平|对话与反思:再论建立批评的中国
·分论坛精彩回顾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文献学
·汉学家李丽揭示波黑汉学新动向,世界汉学
·大道同行,埃及汉学家眼中的中埃合作未来
·《学习时报》刊发刘利理事长署名文章:构
·范军等 | 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战略意义
·美国简帛《老子》研究述评
·《兴隆场》的学术价值与伊莎白的中国情怀
·从中西文化关系的长期发展中寻求文化平衡
·作为研究对象与对话者的情感汉学
·美国汉学家莱尔的学术性翻译及其译者惯习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探索者——宇文所安的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走向均衡的文学图
·20世纪西方汉学界的《诗经》文化研究
·卫礼贤与《易经》研究
·关诗珮:王韬建构的形象工程?——“儒莲
·北美中西比较叙事学理论的建构 ——以浦
·石田干之助的东洋史研究
·新世纪以来海外中国学呈现新趋向
·从”龙“的翻译变化看中文外译新时代发展
·张西平|对话与反思:再论建立批评的中国
·分论坛精彩回顾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文献学
·汉学家李丽揭示波黑汉学新动向,世界汉学
·大道同行,埃及汉学家眼中的中埃合作未来
·《学习时报》刊发刘利理事长署名文章:构
·范军等 | 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战略意义
·美国简帛《老子》研究述评
·《兴隆场》的学术价值与伊莎白的中国情怀
·从中西文化关系的长期发展中寻求文化平衡
·作为研究对象与对话者的情感汉学
·美国汉学家莱尔的学术性翻译及其译者惯习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探索者——宇文所安的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走向均衡的文学图
·20世纪西方汉学界的《诗经》文化研究
·卫礼贤与《易经》研究
·关诗珮:王韬建构的形象工程?——“儒莲
·北美中西比较叙事学理论的建构 ——以浦
·石田干之助的东洋史研究
·新世纪以来海外中国学呈现新趋向
学者访谈/Interview 更多>>
- ·世界汉学讲坛 | 何广思教授解读中拉
- ·阿根廷何广思:超越西方范本才能获
- ·阿尤布: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
- ·黄卓越:早期中国的书写与汉学研究
- ·薪火永相传,著名汉学家马克林讲汉
- ·《人民日报》:《用翻译架起中葡文
- ·蔡宗齐(美国):开辟中国文化走向
11 月 22 日下午,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北京语言大学主办、世界汉学中心承办的世界汉学讲坛第九讲成功举办。本次讲坛由...
10 月 18 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
日前,由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牵头建设的土耳其汉学家理事会在青岛正式成立,土耳其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土耳其著...
摘要:该文原为作者2021年10月20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举办的一带一路汉学研究论坛上所做的现场演讲,对海外汉...
2023年6月7日下午,薪火永相传大师说汉学暨世界汉学讲坛第四讲成功举办。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
2023年02月0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7版刊登了《用翻译架起中葡文化交流的桥梁》一文。文章由新汉学计划海外高级中...
天下学问一家: 开辟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新路径 蔡宗齐 蔡宗齐(Zong-qiCai),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校区东亚语言文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