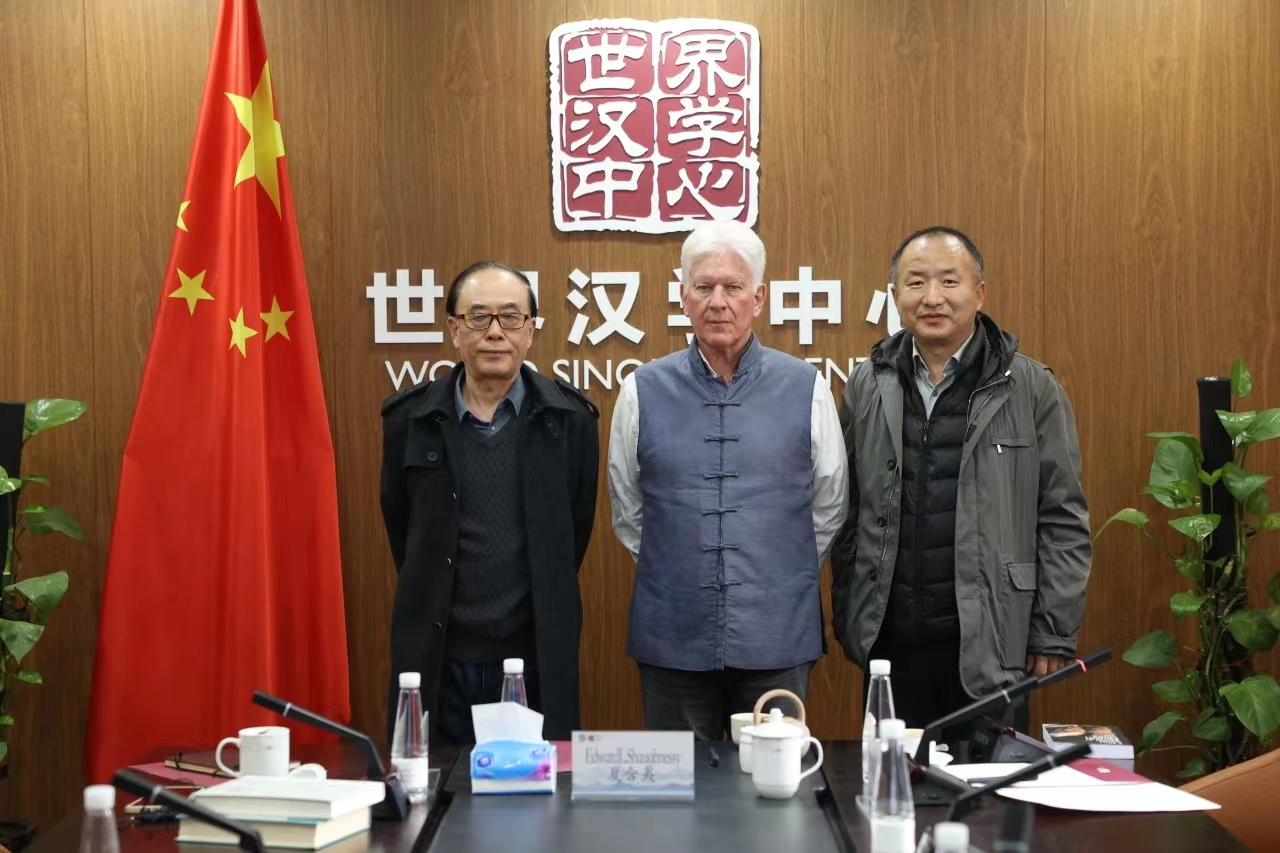黄卓越:后儒学之途:转向与谱系
一
大陆儒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新复炽以后,迅速成为知识界的一种言说主题与思想趣味,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与之相关,最值得回忆的事件有二,一是为儒学价值做出激烈声辩的“反激进主义”思潮,二是对“新儒学”的介引与探讨。以后者而言,最主要的意义还在于学理系脉上的补课,以便与历史及海外的研究进程相衔接,这也使大陆儒学能够以新的气象重新返回于创新性阐释的轨道。然而,从国际的范围来看,新儒学实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即已出现危兆,被称为新儒学最后一位大儒的牟宗三宾天以后,更加速了这一曾主导约一个世纪的思想潮流的衰退,与之相随,各种新的话语纷杂以出,竞相争执,儒学研究遂进入了一中心匮乏的多元言说时代。
时至今日,情况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但并不等于说,在这众多的声音中无法寻找到一些基本的线索(或问题解答模式),以便对新儒学之后的思想变动做出一种有相对规则性与谱系性的描述,并借之而构建出一些新的理解性范型,从而将儒学的“世系”延续下去。其中,儒学与后现代关系的论说及由此构成的言述系统,将成为值得关切的一脉。
儒学与“后现代”能放在一个平面上来言说吗?这个提法乍看起来有些新奇,但如果考虑到后现代体验与知识场域的业已形成及对我们当代生活、观念等带来的重大影响,那么这种关联就会是事实存在的。从一种学术与思想形态构成看,可将之看做是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冲动,一是由后现代的视角产生的对儒学的期望。“期望”这个词,源自郝大维(David L. Hall)与安乐哲(Roger T. Ames)二教授前几年出版的一本著作《期望中国》(Anticipating China)的译名,但显然不限于西方对中国的期望,也是渐次展开中的中国当代化境况与思想实践对儒学的一种期望,以期儒学能够在新的召唤方式下更生,对合理世界的重建有所裨益。尽管这一开始就是一个多义性的问题,但却表明了无论是后现代还是儒学都具有自己的开放性,从而使儒学与后现代这两种原来在时空上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件或学说之间产生一种新的“接合”(articulate)。再一是从儒学位置出发的向后现代的切入,在这种情况下,儒学不再被单纯地看作是一种既往的传统,而是作为一种有自觉、活跃意识的思想与行为的连续体而存在着,这个连续体在宋明以来是以理学(心学)的名义出现的,在上一个世纪则是以“新儒学”的名义出现的,然而在一种已经迅速展开的后现代语境中,儒学如果还希望保持自身这一连续体的创构性活力,即不单单是视之为过去的思想,而是主要作为今天的思想,介入到时代的有效性对话之中,那么就需要站立在这个逐日浮升的后现代的地平线上,来组织自己的学说,构建出新的理论语态,这同样造致了儒学与后现代之间的一种关联。
从目前来看,对二者关联的理论性表述,大致已经形成一种潜隐的趋势。言其“潜隐”,是因为虽然这一思想潮流已经处在一种有力的生成状态,但由于缺乏学术史层面的关注与刻画,及对之的必要的概念化命名,其真实的流脉依然被遮蔽在杂多的言述之中。因此而有必要将之做一相对完整的梳理与疏解,以便使其能从潜隐的状态中走出,于众多儒学言说中清晰地凸显出来,提升为一种可以明确感知的话语趋势,进而有助于对“新儒学之后”整个国际儒学研究走向的把握——此即本文的意图之所在。鉴于儒学研究长期以来的“国际互系性”及地域化差异,可将目前全球范围内与之相关的论述划分为三大板块,即以中国大陆、海外中国学者、海外汉学家为主的三个新的儒学话语圈,与之相应,也就会在对待后现代的态度上存在着三条同中有异的话语路径。
二
最初开始从后现代的视角关注儒学,从而将两种思想系统粘连在一起阐论的是西方汉学家。这种敏感性取决于西方后现代思想本身的前置性。郝大维曾经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明白无误地指出,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中可以发现“非常真实意义上的”“后现代”要素,[1]甚至在更早一些,即1987年,郝大维与安乐哲合著的《通过孔子而思》(Thingking Through Confucius)一书的结语部分,就宣布“赞同西方思想文化属后现代的主张”[2],并指出他们的研究实际上处于两种思想(后现代与儒学)的交汇之处。同时,英国著名汉学家像葛瑞汉(Angus C, Graham)等也在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就开始从相近的视野探索中国古代的早期思想。1986年,葛瑞汉在对史华兹(Benjiamin Schwarts)所著《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1985)一书的评论中,对汉学界以中西间的“相通性”来看待中国思维的权威观点提出了挑战,突出强调了中国古代思维与西方近代思维之间存在的差异,[3]可看做是西方汉学界思想转折的一个重要信号。葛瑞汉对先秦思想的多家文献甚稔,在1989年所著的《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一书中,用德里达对西方理性传统中对立链条的解构方案来分析与老子的相似性,而他所谓的孔子强调的不是人性的本质(“性善”)而是人性的可塑性;孔子并没有一个宇宙论的兴趣或通过对抽象概念的沉思建立一个完整的人生观,而主要关注的是人事的协调;宇宙论的沉思虽然源于古希腊哲学,但在中国只是到了汉代以后才成为思想的主流,直到250年以前,它仍属于在各种哲学流派以外的宫廷史学家、天文学家、占卜者、医师与乐师等的兴趣领域——凡此历史的证断之后均暗含着一种不同以往中国研究的解构论思维。
当然,在此之际,如果从更为贴近的西方儒学研究史的脉络来追溯的话,还必须着重注意到另一人物即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的创辟性工作。芬格莱特也是葛瑞汉《论道者》一书在阐述孔子思想时引述最多的一个学者,被看做是专业哲学家中最早意识到“孔子对当代哲学的可能性的意义关联”的第一人[4]。在其富有卓识的著作《孔子:即凡入圣》(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 ,1972)及继后发表的一些论文中,芬格莱特认为西学在一个时期所处的强势性地位,不仅使西方学者,也包括中国学者在内,在对孔子的研究中羼入了一种迎合这种强势方式的理解,比如现存的对《论语》的翻译,所引入的并不是孔子原有的思考方式,而如真实地来看,孔子的观点则具有某种鲜明的非欧洲人的特征。从恢复孔子的原貌入手,芬格莱特从多方面对孔子关于“礼”、“仁”、“道”等的说法作了独特的理解,并指出其与西方传统思想的根本区别。比如西方哲学倾向与将个体及其自由与理性的意义本质化与普遍化,但孔子的看法不是这样,对于孔子来说,个体既不是真正人性的终极单位,也不是人的价值的终极依据,任何生命都没有超越价值,与之相反,正是与一个人的生活或死亡的情境和方式有关的某些东西,才可望具有终极的价值。“我的生活”实质上是由你和我、我的妻子和我、我的孩子和我,以及我的学生和我等等的生活关系所构成的,当“我”被从我们共同的生活中抽象出来之后,作为人的“我的生活”就失去了其实质的内容,于是我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抽象物,至少就人的本质而言是这样,因此我与人的本性只能是被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关系所确认的,其中如人类经验的“礼义化”便是一种最重要的方式。在孔子那里,也不存在西方思想中长期依赖的事实/价值、内/外等二分逻辑以及将某种概念,比如“仁”等加以心理化的倾向,应当更合适地“把它(仁)设想成为作用于公共时空行为中的一种有方向的力量”,是各种不同向量(the separate vectors)的一种集合[5]。与葛瑞汉后来阐述的一样,芬格莱特以为,将孔子思想做心性论、本体论等的解释,以致使孔子失去了他原来的面貌,这来源于中西两个方面的多个阶段的多种原因,从而历史地将孔子塑造成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样式。而对之的再次重读,尽管芬格莱特没有直接措用后现代的理论概念,但他承认“孔子思想中有着十分重大的类似于西方新思想的成分”,“在精神实质上接近于这种西方哲学最新发展的一些最显著的特征”[6],以此而表明了他对西方新近思潮的认同及这些思想对之可能发生的影响,而他将中国思想与当代西方问题关联一起,及在《论语》研究中生发的诸多新见,均激发了后继者在同一领域所展开的研究。
根据安乐哲回忆,他早年在香港学习中国哲学,并曾受教于在新亚书院讲学的唐君毅与牟宗三等,在伦敦大学接触到葛瑞汉的“关联性思维”的观点,至夏威夷大学后与著名哲学家郝大维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并合著有六种著作。[7]郝、安二人的研究基始于对西方思想的反思,他们认为西方哲学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传统,一是形而上学的“唯一论”哲学,以为人的生命中有一唯一设定的前提,这也是西方思想的主流,从柏拉图到基督教,并深刻地影响到现代性思想的确立。另一是过程论哲学(这是一个简约性的说法),大致发端于达尔文,下传于尼采、怀特海、杜威,再至当代的罗蒂,这也是一个在西方被长期边缘化了的传统,需要在新的时代中重新发掘以使之光大于世。在郝、安二人的论述中,“过程”(Process)是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过程不同于一个命定的单一本体,而是一种连续性的创生活动(Creativity),这差不多等同于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所描述“延异”。与之相关的第二个概念是“关联”(Connectivity)。关联的基础是个体(“多”),而不是整体(“一”),个体总是处于过程与场景之中,因此是一个未定义的成分,它只有为关联所定义,这样,个体与个体就都是不一样的。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提出了一个“协同创造”(Co-creativity)的概念,即将创造与关联并置于一起,为此也可以说,意义,包括了人性的意义等,从来就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协同创造出来的。他们重视的第三个概念是“美学秩序”(Aesthetic order),以此而与“逻辑秩序”相对,美学和谐也是与关联性思维相关并表现出独一无二的与场景化的等特征。在安乐哲与郝大维看来,以上阐述,与当代哲学中众多的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新实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哲学等一起(当然这些都可归入到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范畴中),起到了对本质论哲学持续批判的功能,从而保证了西方思想的活力。如此而再来观察中国古代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思维方式,安乐哲与郝大维以为,后者恰巧表现出了与过程论哲学相吻合的某种倾向,“像怀特海和杜威一样,古代中国的宇宙论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唯一的创造性是一种境域性的共同创造性’”[8],这也可引申到对政治领域比如“民主”等问题的考察,比如可以通过杜威而重新发现他与孔子在社群观上存在的异同点,进而也可以延伸到对后来的唐君毅等一些观点的考察。因此,中国哲学在目前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可以在西方哲学的叙事中提供一种有益的涉入,形成对欧洲中心论及其超越论哲学的批评,与之同时,中国思想也将会在这一关照的光亮中得以复兴,走向一条与西方哲学进行创造性互惠的道路。
要想全面评价安乐哲与郝大维已建立起来的体系庞大的理论工程,涉及到许多方面的知识,也包括史实论证与语境对位等的问题,不属本文的任务。现仅以其关于“一”与“多”的关系之说来看,其思想很显然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试图消解唯一论哲学的超越性设定(作为宇宙万物之上的实体),从而为个体性、具体性松绑,其中自然包含了对积弊已深的现代性意义模式的一种反思。根据郝、安的观点,西方由古典发展而来的主导倾向,是将一与多捆绑在一起,现在则可使多脱离一。但是在多于脱离了一的制约之后,我们所要求的秩序又何在呢?郝、安提出的一个方案就是“关联“、或称之为“互系”,即多与多之间在特定时空或场域中的关联,由此而形成更合理的秩序,既然这个在互系中呈现的多已不同于在一所支配下存有的多,因此又表现出了其创生的延续性,这也就是解构与重构的并置、共生,而没有导致对解构之局的沉迷难返,由此,也就将普遍性与反普遍性同时屏蔽了,体现出了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姿态。
在今天,在北美的学术范围中,借助由后现代的问题视角出发来考量儒学已逐渐成为一个热点,关注的要点也包括儒家在内的多元对话、儒学思维的社会学与政治学运用意义等。如曾与史华兹、安乐哲均有合作的著名儒学思想家的罗思文(Henry Rosemont)教授近来对西方政治与社群问题的关注,就是从对一具有核心意义的价值观的重新考量开始的。他以为西方意义上的第一代人权主张是建立在抽象的与本质化的个人自由的定义上的,虽然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也包含着道德上的阴暗面,即忽视了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地位,为了克服这个定义的盲目性,就有必要引入传统儒家对人的认识。他以为,在儒家看来,自我不是指一个自由、自治的个人,而是在各种关系中所表现的自我,我们也只能通过与其他人的相互作用来达到幸福等的目标,这种思想将有助于纠正西方政治活动中的不良原则。自芬格莱特对儒家之“礼义”之说做了新的阐释,即将之看做一种在广义上而言,及与生活经验密切关联的公共交往系统之后,如安乐哲等人更从互系论的角度对之做了接续性的研究,罗斯文的研究也指出了,对孔子来说,社会调节是十分重要的,而不是交由政府来承担,更好的做法是让传统(“礼”)来承担作为一种民众活动的约束性力量。贝淡宁(Daniel A. Bell)教授则细致地考察了中国古代的礼对公民社会尤其是底层民众在维持实用主义的公正性中所起的作用。在这样一个论述平台上,我们应当看到正是导入的一种对人性关系的新解释,从而为后现代公正论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援。[9]
在欧洲大陆,儒学的探讨虽然相对滞后一些,但也有如著名法国汉学家、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表现出的与北美汉学界相近的旨趣,从其1989年出版的《过程还是创造》(Process or Creation ),至后来的《迂回和进入:中国和希腊的意义策略》(Detour and Access, Strategies of Meaning in China and Greece, 1995)、《圣人无意》(A Sage Has No Ideas,1989)等一系列著作看,弗朗索瓦·于连一直持续探讨的一个中心问题便是中国思想尤其是儒学与西方形而上哲学之间的差异,这也是与史华兹等的思考路径正好逆行的,借助于比较的方式,于连发现中西方之间存在的主要差异就在于中国思想家之把握世界与生活,是用面对现实的“智慧”的方式,而非像西方哲学家使用的是抽象的理论或云“观点”(idea),中国古代圣人的文本均带有一种不确定性,因而也就融合了多种可能性,成为一种开放的体系,不同于西方哲学所热衷的一元本质主义。如做进一步的分析,于连的看法与法国本土的后结构主义具有学理上的深层联系,但就保守的欧洲汉学界来说,则容易视其为一种叛逆性的异端,因此于连的研究在近年来遭到了旧汉学的非议,这种看似儒学或汉学内部的争论,实际上与各自对待后现代的姿态是有甚为密切关系的。
三
现在我们可以将目光转向大陆以外中国学者的研究。与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从西方本身的问题出发,即在西方思想进展的逻辑延长线上切入儒学的后现代思考有所区别,海外中国学者的儒学面向有其自身根基的背景。这个背景包含了他们所处的位置与身份等,如做更细致的观察则各区域之间也有差异,比如北美与东南亚华人所具有的“流散”(diaspora)化特征,台湾知识界则面临一个本土的现代化、民主化问题,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他们融入到其思想中去的方式与特色,然而从一种学术的系脉上来看,则又几乎都与新儒学有着很深的渊源。虽然早期新儒学发端于中国大陆,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政治的原因,儒学飘零于海外,香港、台湾与海外华人世界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灵根再植”之地,后期新儒学即主要是在这些地区延续与发展,并在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的创建性工作中开拓出一开阔的局面,形成了一条渊源深厚的学术思想血脉。近些年来,海外新儒学一系出现了一些蜕变,这些变化,有以称之为“儒学第三期发展”或“第三代新儒家”的,也有命名为“新新儒学”、“后新儒学”的,在相对年长一些的学者中,代表性的人物有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他们目前依然活跃在儒学路向的开拓上,并在思想特征上显现出与唐、牟、徐等前辈的一些差异,在全球化与后现代浪潮的冲击下有相应的调适,这体现在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对象、处理问题的方式等多个方面,进而表呈为向新的学术形态过渡的征况。
这一蜕变,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儒学参与多元对话的热切关心上。关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儒学的应世与创新的可能,因此,即便是新儒学早期的代表人物,也将中西之间的比较与融汇作为其努力的一个方向,或者可以说,新儒学正是在与西方思想的碰撞与吸收中,形成有别于传统儒学之思想特性的,如张东荪等以其所擅长的德国思想来论述其本体论的观念,唐君毅以一种康德“先验推论”和胡塞尔想象学的方法来推演一个有道德意识的宇宙存在,冯友兰受到了罗素新实在论的影响,牟宗三则经由康德哲学建构出“两层存有论”的学说体系,等,在他们的学术构型中都传递出了与西方对话的声音。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对话是建立在中西(或西方与西方以外世界)绝对二分、及西方一元现代化论的思维模式下的,因此所选择的拯救路径也多是以更早的传统性来批判、弥补或融合现代性。相比之下,新近出现的儒学对话论则有一个多元文化的观念背景,并是在这一弥散的框架中进行的,这与后现代主义对一元基础主义、单线进化论、西方中心主义所做的理论消解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而新的儒学对话便能够在一个更为广阔与多样文化并存的概念界面上、及在对多种现代化途径认可的前提下展开。依我所见,既然对话永远只是一个过程,那么,也就等于默认了所有的方案都只是一种局部性的、处于进行式状态的建议。与之同时,新近的儒学对话论,也更多表现出解决整个人类共同问题的视野,这个思路与当代西方后儒学所表达的想法具有相通性,即儒学不限于“本土之用”,也同样承载“全球之用”,由此而可建立起一种新的“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与“局部知识的全球意义”之间的辨证关系。[10]
向新的话语形态的过渡,也体现在对现代性的反思,及要求能够结合考虑后现代的语境与思维,以重新调整儒学的进路等一系列相关的申论上。前一代新儒家因面遇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机轴,因此而试图从内外两个进路上回应这一挑战,即在对外的一面,引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开出一个“新外王”的格局;在对内的一面,依据于传统儒家言述而构建出一个“内在性超越”的道德心性本体,以此抗衡现代化于精神秩序上的紊乱(对应于西方古典哲学的先验论模式),并最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良性对接。然而第三代新儒学却对西方的现代性理念本身(而不单是现代性引起的现象)及其所包含的单线进化论等有不同程度的反思,如刘述先所述:“不只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一元论早已被扬弃,乃至康德所继承的启蒙理性,在现代走向后现代之际,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11],由此而反观第二代新儒家,无疑,牟、唐等所构建的观念化体系也已经在时代的嬗变中渐显落伍。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第三代新儒家提出参考性地关注后现代诸思想趋势的意见。在近来的论述中,成中英即认为儒学的转化应当直面后现代到来这一事实,对现代性进程中出现的弊端提出解救的方案,利用后现代所提供能动作用:“使其自身和现代性创造性地转化为一个服务于人类社会和人类自我的统一体”[12]。杜维明在反思现代性及提出“超越启蒙心态”的同时,以为应当正视“为我们提供了继承启蒙精神和超越启蒙心态的新思维和新契机”的当代西方四种思潮,即生态意识、女性主义、宗教多元以及全球伦理,[13]并在此迎受中推进儒学话语的更新。
但这并不等于说,当代新儒家已经完全接受了后现代的主张,与后现代思想并步以趋了,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代新儒家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对后现代也同样会持有一种慎谨的保留,甚至批评。更重要的是,由于与前代新儒家的密切渊源关系,在一些哲学的基本立足点上,他们仍然很难超出前辈的设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本体超越的主张。无论是杜维明还是成中英、刘述先,虽然他们各自向后现代观念开放的程度不一,以及对心性回归的论证究竟是一种最初的根据还是末了的归属——意见也不一致,但最终都不约而同地是会回到牟、唐等所确立的那个作为内在超越之精神本体的“第一逻辑起点”上,这似无须再多做引证的。就此而言,也就难以突破儒家固有的心理本质主义,“多”的呈示依然要回归于一个以“一”为标志的“理一分疏”的潜在结构之中。尽管在他们的论述中已更多地注意到社群的功能,但这种“关系”或“关联”却不是“接合”(articulate)性的,而是依然要从决定性的心体或主体启程的;依然不是美学式关联的,而是因果逻辑式关联的。由此,我们再次看到其理论与西方后儒学之间的差异。因此,如果说第三代新儒学有一个趋向于后现代视野的转移,勿宁将之看做为一种过渡与试探。
言及于此,还应当提及在台湾更年轻一些学者中所发生的变化,比如林安梧与高柏园,在思维上有更超出所谓“第三代新儒学”之处。林安梧受教于港台新儒学的前辈,然近年来则以“后新儒学”命说其思考的取向,这表明了其在“新”儒学的承接上向“后”形态渡越的明确意识。在肯定新儒学历史贡献的前提下,林安梧对儒学的心性本质主义有一系统的症断,以为从“内圣”到“外王”的进路,不唯虚设,而且也易落入以“心性修养”为中心,终至将儒学玄学化,而遗弃儒学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公正”的面向;为此而提出,可将旧儒坚持的由内圣而至外王的路径,反转过来调节为以社会公义为中心的由外王而至内圣的路向,以达以自为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为启点,以整个生活世界为场域,以历史社会总体为依归的新境地[14],由此突破新儒学面遇的困境。高柏园所撰《后儒学的文化面向》,已明确以“后儒学”的概念来指认儒学当代儒学发展的特征,并借助“异质”与“非连续性”等概念来阐述时代进程的特点,而以为后儒学的重点即在于关注这种异质与断裂的状况。就儒学的范式转型而言,高教授以为“后儒学并不是后牟宗三哲学,而是有着完全异质性的发展可能”,是“新范式与旧范式的不兼容性”[15],具体又表现为不再局限于过去的以统一和判教为前提的思路,而是表现出对“实践之知”的重视,能够回应急剧变化的时代问题与挑战,在全球化场域中设定自己的对话位置与问题意识,走出儒学“哲学”化的单向定位,获取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综合性视野等。就以上这些简单的描述来看,台湾的当代儒学探讨已开始摆脱新儒学投下的巨大身影,而走向一种更具时代品性的重构之路。此外,再一需要注意的是有些长期旅居北美的华人学者,其学术上的渊源比较复杂,在身份确认上也有异于港台的学者,因而相对难以归类,比如田辰山、梁燕城等,于近年来在对儒学转向问题的探讨上也表现得十分活跃。以田辰山为例,他早年从大陆赴美,后长期在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同时又穿插往返于大陆学界,因此,既有中国本土的生活与学术根基,又受到北美儒学的较深影响,也有将之思想归为“夏威夷学派”中的。田教授主张以后儒学的视野平议中西,但同时认为即便是儒学与后现代之间存在着契合,也依然应当注意到其间的结构性差异,像二元论、本体论、实质论、普遍主义等哲学思维工具,是西方的特定产物,仍被挟裹在后现代主义之中,因此需要诉诸不间断的对话,以此来重建本土自身的话语思想体系,而如早期儒家中所包含的通变、互系等思想即可纳入到后儒学的论说系统之中。
- ·世界汉学讲坛 | 何广思教授解读中拉
- ·阿根廷何广思:超越西方范本才能获
- ·阿尤布: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
- ·黄卓越:早期中国的书写与汉学研究
- ·薪火永相传,著名汉学家马克林讲汉
- ·《人民日报》:《用翻译架起中葡文
- ·蔡宗齐(美国):开辟中国文化走向
11 月 22 日下午,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北京语言大学主办、世界汉学中心承办的世界汉学讲坛第九讲成功举办。本次讲坛由...
10 月 18 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
日前,由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牵头建设的土耳其汉学家理事会在青岛正式成立,土耳其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土耳其著...
摘要:该文原为作者2021年10月20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举办的一带一路汉学研究论坛上所做的现场演讲,对海外汉...
2023年6月7日下午,薪火永相传大师说汉学暨世界汉学讲坛第四讲成功举办。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
2023年02月0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7版刊登了《用翻译架起中葡文化交流的桥梁》一文。文章由新汉学计划海外高级中...
天下学问一家: 开辟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新路径 蔡宗齐 蔡宗齐(Zong-qiCai),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校区东亚语言文化系...